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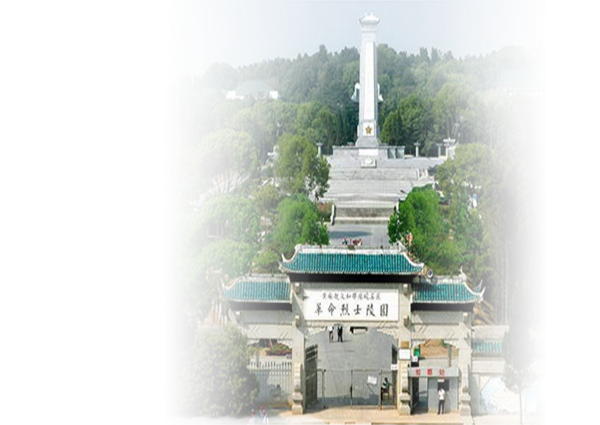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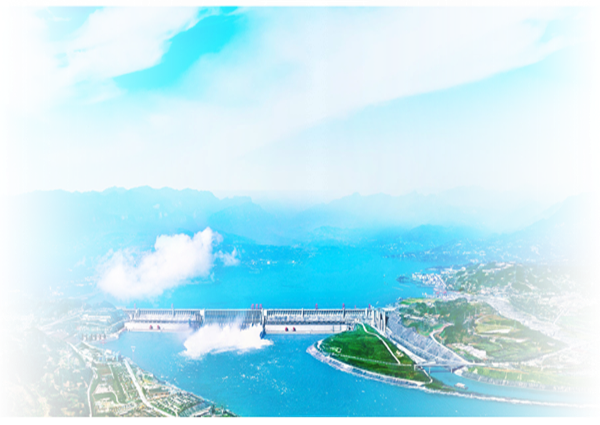
李幼华
李幼华,女,原籍河北省乐亭县,1938年出生于哈尔滨。1943年,随母亲回到原籍。1945年随父母去东北。1959年,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物物理系。1964年,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干部局工作,此后一直从事科研及管理工作。1998年退休。
发生在我们家的那些真实的故事,也是中华民族抗战记忆的一部分。那时我是一个孩子。我从小孩子的角度看见的、听到的,到今天已经成为故事。虽然是普通人、平凡事,但是也留下了历史的记忆。父母给了我生命,养育我成长,为我做出了榜样。我把这些故事记录下来,让后辈人了解,以此寄托我对父母的怀念。
我的家庭
1914年3月24日,我的妈妈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汤家河张各庄一个农民家庭。我的外祖父叫李琢章,是一位厚道善良的农民,朴实勤俭,颇受乡亲们尊敬。
妈妈说,当她15岁的时候,就由父母做主嫁给了还在上中学的我爸爸。结婚以前他们两人根本不认识,从未见过面。婆家在离张各庄13里的胡家坨乡大黑坨村,李大钊故居就坐落于此。
我爸爸叫李振华,家在路北偏西头,李大钊故居是路北居中,爸爸管李大钊叫大叔。因为是一个家族,两家房子的砖都是一样的,门口都有一棵老槐树。我爷爷叫李寿田,一生务农。因为爷爷的大哥李瑞景早年闯关东,在黑龙江和俄国人贩牛、办酒厂,在老家盖了房子,买了地。所以爸爸的家庭出身填写的是“地主兼商业资本家”。我大爷李瑞景是位开明进步的人士,曾秘密帮助李大钊到苏联去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新中国成立后,大爷将全部资产都捐献给了国家,他是黑龙江省第一届人大代表,1954年因公殉职,被省人民政府追认为烈士。因为他没有儿子,我爷爷有四个儿子,所以说好将我爸爸过继给了他。
我爸爸比妈妈大两岁,1929年他结婚时才17岁。这一年,他正在天津参加革命组织反帝大同盟。此时他已经开始研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结婚后,妈妈改了名字叫文华,两家都姓李,所以爸爸妈妈一个叫李振华,一个叫李文华,由此也可见他们感情之深。抗战时期爸爸的名字已经改为李海涛,但是亲友和家乡人民还是叫他“振华”,他还有几个名字—黎文、高继祖等,是做地下工作时的化名。
我父亲为族叔李大钊办理丧事
1933年,爸爸从北平志成中学高中毕业。当时,北平地下党正准备为被反动派杀害了六年还没有安葬的中共领导人李大钊举行葬礼,而李葆华(李大钊长子)正被敌人通缉,不能出面办理,地下党安排我爸爸为族叔李大钊办理丧事。
李大钊是我爸爸的大叔,他被反动派杀害后,我爸爸非常难过和后悔。此前有一年暑期,李大钊回了老家,我爷爷让他去看望大叔,他不去。因为他对当时腐败卖国的统治者不满,不愿去看一个“当官的”。李大钊牺牲后,他才知道大叔是一个革命家。他非常钦佩大叔的伟大人格和英勇献身精神,要继承先烈未竟的事业,冒着生命危险承担起为李大钊办理后事的重担。他回老家接来了李大钊的遗属,出面办理葬礼手续,并在4月23日这一天,当孝子穿着孝服打着幡走在灵车前面送葬。
这葬礼实际上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李大钊的灵柩从宣武门外浙寺起灵,沿途有许多北京市民自发加入送葬的队伍。有工人、农民、教师……过了西单游行示威的队伍人更多,人们喊着“李大钊先烈精神不死!”“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送葬的群众边走边撒纸钱,上面印着抗日救国的口号,人们时而唱起悲壮的《国际歌》。人民缅怀烈士英灵,沿途商店门口摆上了祭桌,摆着点心水果,烧着香举行路祭……到西四牌楼,反动政府派出了大批军警、宪兵、特务,还有马队,他们用大刀和水龙驱逐和抓捕游行示威的人,数十人被捕,示威群众被打散。我爸爸一直打着灵幡,走在灵车前面直到香山万安公墓,将烈士安葬。
办完李大钊的葬礼后,爸爸受到反动政府注意,在北平的住处被特务搜查。此后爸爸就决定不考大学,离开北平回到了乐亭,以教书为掩护从事抗日工作。同年,爸爸在乐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爸爸改名叫李海涛。1933年,我的大哥出生,这时爸妈结婚已经四年了,爸爸总是把革命工作放在第一位,四年中他们共同生活在一起的时间很短,这四年正是爸爸革命生涯的开端。
父亲在华北参加抗日斗争
爸爸参加革命以后,妈妈就成为他最可靠的助手和战友。妈妈虽然只是一个家庭妇女,但她很有正义感,而且很有智慧。加上爸爸常给她讲一些革命道理,使她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革命家的忠实伴侣。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北三省,进一步向华北地区“蚕食”。我们的家乡和东北只有一关之隔,因此早在1932年就有日军横行了,共产党在这里的抗日组织工作也较早。1933年,我爸爸来到家乡工作,担任中共乐亭县委宣传部长,秘密组织发动群众抗日。1934年冬,党中央派来一位老红军领导检查指导冀东的工作,我爸爸安排这位同志住在自己家打谷场院的小屋里,那里僻静,比较安全。爸爸让妈妈负责送饭和照顾这位同志,家里其他人谁也不知道。妈妈虽然一生没有正式参加党组织,却很早就为革命作贡献。
1935年,爸爸被党组织调到天津,担任全国总工会华北代表处天津市工人联合会特派员,从事更危险的地下抗日情报工作。他的直接领导和单线联系人是后来担任北京市市长的吴德,爸爸在北平上学时曾和他租住同一间房子。爸爸从事秘密抗日情报工作,妈妈根本不能和他有任何联系,也不知道他在哪里,所以这是真正的分别。
1935年8月,爸爸在天津因叛徒出卖而被捕,这个叛徒就是他的下线联系人。当时,他按约定来接头,走近接头地点时,感到情况不对,因为发现前面还有一个人。他马上回头就走,但是后面早有特务堵住了后路。叛徒指着爸爸说:“就是他!”就这样爸爸被捕了。敌人审讯时,叛徒又指证他的身份。爸爸说:“我是共产党员,要抗日。你们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敌人严刑逼供,爸爸一点党的机密也没说,后被关进天津第三监狱。
爸爸被捕后一个月,妈妈又生了我的二哥,可能为了爸爸能平安回来,起名叫“明安”。妈妈承受着巨大压力,从容不迫地接受了命运的挑战,照常做着一切事情,养育两个儿子。
爸爸在狱中继续和敌人斗争,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英雄气概。他和狱中的政治犯难友—共产党人韩庄、韩培义、王洁清等组成了狱中党支部,组织领导狱中斗争。1936年,组织了两次政治犯的绝食斗争。敌人对他们进行了残酷的镇压,用吊打、灌稀饭、威胁、分化等手段,妄图把斗争压下去,都没有得逞。第一次绝食坚持了五天。爸爸还执笔写了《绝食宣言》和《告全国父老兄弟姐妹同胞书》,宣传抗日,要求无罪释放政治犯。爸爸和同志们的斗争取得了社会的同情和支持。天津《庸报》还刊登了《告全国父老兄弟姐妹同胞书》,《益世报》报道了绝食的消息。记者要求到监狱采访,群众也要来狱中慰问,这次斗争轰动了天津。敌人不得不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作了一些让步,绝食斗争以胜利告终。第二次绝食斗争在六七月份,敌人怕把事闹大,只得答应了条件。
但是敌人很快就把他们分别押解到张家口等不同的地方,分而治之。爸爸在和同志们被押解去天津火车站的路上,高喊口号,唱《国际歌》,宣传抗日,反对外解。火车到达北京西直门站时,他们又组织了卧轨斗争,迫使敌人把他们改押在北平第二监狱。
爸爸的这些英勇斗争的事迹,我们都是后来才知道的。“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对我爸爸毒打、罚跪、饿饭,非逼他承认是叛徒,他宁死不承认。正是这些造反派的调查结果使我们知道了爸爸是这样一个英雄。爸爸从不夸耀自己的事迹。记得我在育才上小学时,学校发了一张表让家长填,调查是否有亲属牺牲、被捕或做过地下工作等经历,目的是找革命传统教育材料。爸爸看后把表放到一边,一个字也没有填,还严肃地对我说:“你们干革命,不要靠死人,也不要靠活人。”这对我教育极深。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全民族抗战爆发。共产党在北平西部郊区建立游击队,并派共产党人参加到东北流亡学生赵侗组织的抗日义勇军里。当时,国民党命令二十九军要在7月28日退出北平前,将第二监狱的所有政治犯处决。中央领导同志通过北平地下党组织营救狱中的共产党人,命令下达到党领导的平西游击队,还有一个解救人员名单,其中第一个就是“李大钊的侄子李海涛”。我爸爸并不知道这一细节。当时执行命令的是平西游击队的队长刘凤梧,后来他一直在军队系统工作,生前和我爸爸没有联系。他儿子刘生津调查这段历史过程中打听到李海涛在天津人民检察院工作,已经去世,才找到我。
赵侗抗日义勇军当时只有20多人,很不起眼。为了补充干部和兵源,他们配合平西游击队冒险到北平第二监狱去劫狱。1937年7月21日,负责营救的队伍乔装成日本人,诈开了狱门,占领了监狱。我爸爸从单人牢房门的小孔看到看守换了不认识的人,警觉到发生了情况。他第一个和义勇军取得了联系,但打不开牢门。他急中生智,将单人房间唯一能动的东西—铁床竖起来,撞击铁门,终于打开了牢门,又用同样的方法救出其他同志和难友。当时救出政治犯五十多人、刑事犯上千人,其中有七八百人参加了平西游击队和抗日义勇军。
出狱后,爸爸参加了赵侗抗日义勇军。他们行军在平西平北崇山峻岭中,和日本人打游击。爸爸说,他们连续作战、行军,天下大雨的时候,雨水顺着眼镜流下来(他高度近视,离不开眼镜),什么也看不见,他只能拉着前边同志的衣服向前走。由于几天不能睡觉,有的人走着走着就睡着了。他在狱中患上了严重的脚气病,行军走路非常困难。三个月后,经队伍中党的领导同意,让他回原籍自己接组织关系。
就这样,爸爸1937年又回到家乡,见到亲人们。这时家乡党组织正在筹备冀东抗日大暴动,爸爸立即被任命为乐亭县委书记,领导家乡的抗日武装大暴动。在家乡,爸爸有很多熟悉的朋友、战友,对敌情民情也都很了解,如鱼得水,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
父亲参加冀东抗日大暴动
1937年底,我爸爸在党的领导下组织筹备武装暴动工作,他的上级领导是李运昌(当时是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冀热边特委书记,后任冀热辽军区司令员)。1938年6月,中央军委和晋察冀军区派八路军第四纵队挺进冀东。7月,冀东党组织发动了早已筹备就绪的20万工农兵里应外合的抗日大暴动。在党的领导下,爱国的工人、农民和其他各阶层人民(包括一些国民党爱国人士、地主和资本家),拿起钢枪、土枪、镰刀、长矛等武器,参加到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之中,向日、伪军宣战。暴动时,乐亭的抗日联军是第十总队,爸爸是总队长,时年25岁。听说,他骑一匹白马,穿一身军装,打着裹腿,很是英武。
我在江西赣州认识一位老红军的夫人,是乐亭人,她曾经跟我说:“你爸爸很会演讲,宣传抗日,动员群众,讲政策方针,很受欢迎。”爸爸带领的军队纪律严明,和老百姓水乳交融,深受群众欢迎。我还听李葆华大伯说,在暴动的七个县中乐亭是第一个打下县城的。李运昌伯伯对我说过:“你爸爸的第十总队是保护司令部的,纪律严明,在部队西撤时,其他部队都被敌人打散了,这个部队没有散。”爸爸也和我说过,当时奉命西撤时,暴动部队共有四支队伍,他的队伍是其中之一。在潮白河边,有三支队伍因敌人围追堵截和战士们思想不通(不愿意离开故乡)而大部分溃散了,只有爸爸这支队伍没有散,完整地保留下来。重新集结的队伍跟着李运昌司令员回到冀东北部山区。敌人卷土重来占领了家乡广大平原地区,暴动队伍转入京山线以北的山区和敌人周旋,在艰苦的斗争中重新发展壮大。其中一段时间,爸爸还曾被派到开滦赵各庄煤矿,帮助节振国进行抗日活动(当时节还没有入党)。爸爸告诉我,在节振国那儿他的公开身份是大师傅(厨师),以厨师身份作掩护。
提起暴动,我妈妈也有一段值得一提的佳话。暴动前,为了组织抗日武装,八路军要筹措经费买枪支弹药。妈妈主动把她陪嫁的嫁妆都献了出来。因为结婚时家境尚好,她有不少首饰和银洋,全部交给了当时的领导人阎达开。新中国成立后,阎伯伯还和我妈开玩笑地说:“我欠的债还没还呢!”妈妈从来没想过要还,她支持抗日活动是义无反顾的,她献给革命的又何止这些首饰银洋呢?
1938年的抗日大暴动中,所有的地下党人身份都公开了。起义队伍离开了家乡,敌人对革命者及其家属进行了残酷的迫害。当时爸爸作为共产党领导干部的身份早已家喻户晓,爷爷家就是乐亭抗日暴动的指挥部,家属也暴露无遗。爸爸和队伍转移后,敌人悬赏捉拿爸爸。敌人还在爷爷家院里扔下一颗炸弹,炸死了两个人。后来,敌人又抓走了爷爷,关进城里宪兵队的大牢。敌人逼他交出儿子,他不交(他也真不知道儿子在哪里),他被毒打,坐老虎凳,灌辣椒水,拔胡子,受尽折磨。家里为营救爷爷,变卖掉了大部分土地和值钱的东西。爷爷家被抄家封门,从此一家人星散逃难。
妈妈怀着八个月的身孕,带着两个儿子到处躲藏。亲戚们也不敢让她长住了,因为随时有敌人搜查的可能。家乡实在待不下去了,爸爸一点消息也没有,妈妈和姥爷商定离开家乡去逃难。因为铁路查得紧,妈妈决定带着两个孩子从水路经渤海逃往东北,投奔在哈尔滨的大爷。
那时的海上运输工具就是木帆船,乐亭也没有码头。大人们抱着孩子蹚水上船。船在海上遇到了风浪,在海上漂泊了三天三夜。小船猛烈地摇晃,从来没有坐过船的妈妈呕吐不止,一连吐了三天,滴水不进。船最终无法航行,又回到岸边。妈妈被抬到岸上时,已昏迷不醒,根本没法回家,就躺在沙滩上听天由命。至于肚子里的孩子,人们已经完全不抱希望了。
妈妈醒过来,静静地躺在沙滩上,眼看太阳就要落山了,同行的人们都纷纷离开海滩回家了。正在绝望之时,来了一辆拉草的牛车,一打听是西海村的。真是老天有眼,救母子活命,因为爸爸的一个姑姑嫁给西海的人家了。妈妈就被抬上牛车拉到了姑奶家。姑奶给妈妈喂了些米汤,妈妈才慢慢缓过来。妈妈是在船上光吐不吃虚脱了,仗着她身板硬,在姑奶家休养了几天就恢复了。
从姑奶家离开,妈妈又带着孩子们回到张各庄娘家。那里是母子温暖的乐园,可也是敌人注意的目标,宪兵队已经传讯过姥爷,姥姥家也不能久留。姥爷暂时把妈妈转移到亲戚家,而后安排妈妈和回东北工作的四舅同行,乘火车前往哈尔滨投奔大爷。有四舅的照应,妈妈一行人顺利地到了哈尔滨。
就在哈尔滨大爷给租的小屋里,妈妈生下了自己的大女儿。那时根本谈不上去医院,就在家里生产。由于受了一个多月的折腾,孩子先天不足,瘦得只剩一把骨头,15天才睁开布满血丝的眼睛。大伙都认为这孩子肯定活不了。在那个战乱的年代,连大人的生存都很困难,就更不用说小孩子了。孩子满月刚过三天,妈妈又不得不启程离开哈尔滨前往奉天(今沈阳市)。临行前,亲戚们对妈妈说:“孩子在路上如果死了,就从火车窗口扔出去吧。”妈妈挤上火车,亲戚把俩男孩子从窗户塞进去。妈妈手里抱着一个女儿,带着两个儿子,坐上了南行的火车。火车上秩序很乱,妈妈坐在靠车窗的一个座位上。孩子一动不动地在被包儿里睡觉。妈妈以为死了,打开小被看,一打开被子孩子就哭,几次都是如此。妈妈见孩子还没死,也不忍心扔下去,就一直抱到了奉天,一路上连尿布也没换过。后来给孩子起名叫滨凤(奉的谐音)。这个大难不死的孩子就是我。
我小的时候,不知听过多少遍这个故事。妈妈晚年,我去照顾她的时候,她又一次深情地看着我,提起这件事,还说:“没想到你还活下来了,还长了这么个大个儿。”我很感谢妈妈的生养之恩。在我五岁之前,爸爸杳无音信,妈妈带着我和两个哥哥在东北亲戚家避难,真不容易。我的生命是妈妈千辛万苦保护下来的,纪念妈妈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她的精神财富传承给后人。
五年逃难生活
从我出生到五岁,妈妈都是带着我们过着逃难的生活,先是在哈尔滨大爷家,后到沈阳二姨家,又到德惠姑姥家,后到长春二姑家……后又回到沈阳二姨家。转来转去,东北所有的亲戚家都跑遍了。妈妈在东三省避难并不是因为那里好,而是那里可以隐姓埋名躲避日军抓捕,保住性命。因为家乡敌人盯得很紧,认识的人太多。
那时东北是日本人统治的“满洲国”,中国人是亡国奴。中国人被奴役、枪杀、凌辱,是家常便饭。中国人只能吃“混合面”(橡子面和糠、高粱等的混合物,吃了很难排便)等粗粮,大米白面是给日本人吃的,中国人吃了就是犯法。妈妈从黑市买点儿米或面给孩子们吃,都十分紧张。听说一个孕妇被汽车轧死后,肚子里流出大米粒子,不但不偿命,家里人还受到牵连。这就是日本人说的“东亚共荣”!
为了活命,人们也只能冒险在黑市买点细粮。有一回在德惠,妈妈刚买了半袋面粉,就听见院里乱糟糟的,一看是伪警察又来搜查了。情况紧急,妈妈机警地提起炕边的半袋面,放到炕头的被垛上,再盖上一块枕巾。伪警察进来,东翻西找,只在放粮食的小木柜里找到一些粗粮,无趣地走了。
妈妈和我们在东北逃难时的生活费用是大爷和姥爷设法解决的,我们穿的衣服鞋子都是妈妈亲手做的。妈妈带三个孩子,还是那么恶劣的环境,困难是难以想象的。但是妈妈保护和养育孩子,从无怨言,而且以乐观的精神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现在还保存的一张照片就可为证。照片上的妈妈慈善安泰,乐观自信,一点没有逃难者的样子。大哥二哥站在两边,穿的是妈妈亲手做的学生制服;我站在妈妈前边,靠在妈妈腿上,穿的是妈妈亲手做的绣花鞋。
除了生活上的种种困难外,当时更大的困难是要时时提防敌人的盘查。大哥二哥都是关不住的男孩了,在外边万一说漏了嘴,那可了不得,妈妈时时要叮嘱操心。例如,别人问:“你爸爸在哪里?”“你爸爸干什么?”都要有事先编好的说法。在德惠时说:“在哈尔滨,做买卖。”在沈阳二姨家的对门住的是一个警察,对我们几个住在这儿,老看不见孩子的爸爸,好像起了疑心。妈妈又让我们说“爸爸没了”,免得别人打破砂锅问到底,孩子们说错了惹祸。我们谁也不愿意这样说。我们想知道爸爸在哪里,干什么,什么时候能见到他,妈妈更是为爸爸担心。这样的日子整整熬了五年,可妈妈硬是挺了过来,真了不起。
有意思的是,妈妈给我讲过一个故事,那是妈妈的一个梦。妈妈梦见爸爸躲在一棵芭蕉树下。她把这个梦讲给姑姥听,姑姥说:“芭蕉,那不是八路军吗!”妈妈觉得有道理。果然不出所料,1943年,姥爷托人带口信说,爸爸是八路军,已经打回老家来了,爸爸派人给姥爷送信了。
回到敌后抗日根据地
1943年,我已经五岁了。姥爷带信到二姨家,告诉妈妈我们可以回老家了。跟着妈妈回老家的情景我记得不多,只记得从昌黎下火车,乘坐马拉的胶皮轮子的大车。中间还过了一条河,就是滦河。河上没有桥,大车是蹚着水过河的。
正行进时,突然树林中冲出几个手持红缨枪的人,拦住了路,盘问车上的人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原来是到了八路军的地盘了。听过我们的回答,盘查者好像知道我们是八路军的人一样,变得十分热情。我们也觉得松了一口气,可算到解放区了。大车把我们一直拉到姥姥家。
后来知道,这时期,抗日战争已进入相持阶段。我爸爸奉命开辟路南根据地,包括昌黎、滦县、乐亭等几个县,后任八路军冀东军区第十七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地委书记,那时,爸爸的队伍就在家乡农村一带活动。日军只占据少数据点,广大农村都是八路军控制。
这以后,我们就跟着爸爸打游击了,有时在这村,有时在那村,有时和爸爸在一起,有时把我们安排在老乡家。妈妈除了照顾我们孩子外,还负责保管文件,还管理部队的伙食。1944年,妈妈又生了一个女儿,就是大妹妹。大妹妹出生的那个村子因为名称很有趣,所以我记得,叫“王八赶庄”,听说是因为发水赶着村子随河岸迁移而得名。
我的家乡冀东是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一部分。八路军神出鬼没地打了不少胜仗,斗争的胜利和老百姓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八路军打日军,老百姓真心实意拥护八路军。八路军也是真心实意为老百姓,在广大农村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实行了减租减息。那时候,群众工作做得深入人心,儿童团、妇救会、民兵抗战的积极性可高了,站岗放哨查路条,做鞋做饭搞拥军慰劳。抗战的歌曲男女老少都会唱,像《歌唱二小放牛郎》《红缨枪》《八路好》等等,我都是那时学会的,至今都没忘。
还有一点感受我觉得很可贵,就是那时人人平等的气氛。长工翻身有了地位,东家也得尊重几分。普通农民可能就是干部和党员的救命恩人,八路军的胜仗可能就要依靠某个百姓的情报。今天是老百姓的小伙子,明天可能就参了军。在民族危急存亡的重要关头,大家目标一致,团结一心。八路军代表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人民拥护八路军,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当时农村经济还比较活跃,解放区社会治安也较好,不但惩治汉奸恶霸,还改造流氓懒汉,真的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老百姓不但有饭吃,还供养八路军(因为八路军没有军饷)。总之,是一派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气象。
在抗日根据地战火弥漫的土地上,让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是八路军和老百姓的鱼水情,像我们这些人也是老百姓掩护才活下来的。爸爸给我讲过两个真实的故事:一个故事是关于一位英雄老村长的。八路军一位伤员隐蔽在一个村子里。日军来了,把老百姓都赶到麦场上,追问伤病员的下落,老百姓都不说话。日军把老村长叫出来。这位老村长表面是给日军办事的,是伪村长,实际是向着八路军的,是我们的基本群众,当时有很多这样的“两面政权”。老村长知道八路军伤员在哪里,但是不告诉敌人。敌人把他绑在大树上,把刺刀顶在他的肚子上,威逼他“不说就刺死你!”,他还是说不知道。敌人用刺刀挑开他的肚子,他在最后时刻两眼睁圆,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他用自己的生命保住了八路军战士的生命。爸爸说,当时他还在战地小报上写过一首诗,赞扬这位英雄农民。另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位妇女。有一位伤员在她家养伤,日军来搜查,问她:“炕上的是谁?”她说:“是我男人。”日军不信,要试试她,叫她和男人亲嘴,她就亲了。那年代中国人很传统保守,日军认为不是她丈夫是不会亲的,所以就走了。爸爸满怀深情地对我说:“这位妇女也很了不起。我们共产党什么时候也不能忘了人民啊。”
作为军属前往东北
日本投降后,冀东的八路军李运昌部奉党中央命令率先出关收复东北。我爸爸和妈妈决定只带着我和妹妹随部队前往,把两个哥哥留在老家了。临别时,在姥姥家西屋安顿事情。爸爸坐在炕边椅子上,我站在爸爸身前,大哥拿着爸的手枪耍弄。爸爸刚刚把我抱到他腿上,大哥的枪就走了火,子弹从我身前擦过,穿入木柜里,真把一家人吓坏了。
我们家属到东北去是坐的火车,沿途我看到好多等待遣返回国的日本移民。到东北没多久,妈妈又不得不转向,带着我和妹妹回老家了。原来八路军走后,老家的汉奸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的接收大员,“还乡团”到处屠杀共产党抗日干部和家属,乐亭有位副县长的儿子已经被杀了。妈妈是冒险回去接我两个哥哥的,她悄悄到家接了儿子马上又返回东北。
返回东北的路上,妈妈带着我们在昌黎县等待火车,住在一个小旅店碰到盘查。两个小特务见大哥是个半大小伙子,就凶狠地问:“你是干什么的?”大哥向来说话就倔,回答:“什么也不干!”“你是小八路!”特务说。妈妈赶紧说:“他才13岁,个子长得高。”可是特务不听,一个特务就把大哥带走了。妈妈正着急,又进来一个特务头子,可把妈妈吓坏了,这人原来也跟爸爸当八路,后来被捕投降当了特务,他认识我妈。妈妈心想:“这下完了。”但还是面不改色,静待事态发展。那人进来后看见我们,先是愣了一下,随后装作和屋里人不认识的样子,转身和小特务说了几句什么,就带小特务走了,不久也把我大哥放回来了。原来这个人虽然跟了敌人,但良心还没坏。再说,出卖了我们对他不利,会暴露他很多关系。这样,我们又化险为夷。后来,他托人给我爸带过来一个字条,说要回到这边来行不行。经过请示,上级批准他重新回到革命队伍。他后来带着枪,从敌人那边又跑回到共产党这边。
过了这一关,坐上火车就到了东北。找到爸爸以后,我们就一直没有离开自己的队伍。我爸爸在东北时,历任黑龙江省防军第一支队司令员兼政委,中共辽北省工委书记,省军区司令员、政委,省委副书记等职。我们是随军家属。
当大部队开拔时,我们家属另有队伍,走得比部队晚一段时间。我们看不见部队的行动,但有少量军人保护我们。有一回,有一个机枪班跟我们一起行动,我们乘大卡车飞速行驶在一条公路上,突然遇到敌人挖掘的壕沟,有一米多宽,汽车来不及刹住,竟然冲了过去。因为强烈颠簸,汽车左侧的车门颠开了,妈妈正抱着妹妹坐在副驾驶座,一下子被摔出去,倒在土路上。妈妈的腰摔断了,可是手中抱着的孩子没有受到一点伤。当时我在大汽车的敞篷车厢里,天特别冷,头上蒙着毛毯,还冻得瑟瑟发抖。出事后我从毯子里钻出来,看见妈妈已被人扶起来,脸上有几处擦伤,当时不知腰椎已经骨折,妈妈还咬牙挺到目的地。后经医生诊断需要做手术,可是天天在行军,没有条件治疗,妈妈躺了一个来月,骨折自愈(但是有错位)。这次负伤成为妈妈晚年瘫痪不能行走的原因。
还有一次是往更北的地方走。爸爸骑马和部队奔驰在雪原上,呼啸的西北风卷着大雪,一片白茫茫。我们坐的是带篷子的马车,里面暖和一些。马车也是在雪原上飞快地奔驰。一次没关好门,冷风从门口窜入,我伸手去关门,不料一个大人的手比我快,一下子把门拉上了。我的手被门挤得血流不止,两个指头皮肉分家,连疼带吓我大哭起来,后来由卫生员给我包扎起来。我也成了小伤病员了,解系裤带也不行了。后来,到了哈尔滨附近一个城市,我受伤的手指甲掉了,长出一个“猴指甲”,我觉得很难看。不记得又过了多久,才长出新的正常的指甲。
在东北的记忆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又发动了内战。1946年,当时国民党进攻我军,来势十分凶猛。形势十分紧张。我们随队由四平退到哈尔滨。
当时,妈妈又要临产,不能再跟部队走了,被临时安顿在哈尔滨一个旧居民楼的房子里。爸爸带着二哥住在松江军区司令部。那时大哥已经离家参加革命,只有八岁的我、三岁的妹妹和妈妈住在一起。不远处还安顿了另一位家属,是妈妈唯一的同伴和帮手。12月16日半夜,妈妈临产时,自己走出去敲开她的门,请她来帮忙。我听到她们说“烧开水”“烫剪刀”等话,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听见小孩哭才知道生下了我的大弟弟,后来取名叫哈生。
当时,哈尔滨局势很乱,到处是土匪杀人抢劫,每天听到的都是这样的消息,直到我军把敌人挡在离哈尔滨不远的双城以南,局势才稳定下来。此后,我们搬到了东北局所在地—哈尔滨南岗的一座七层大楼里住,那里有警卫站岗,有现代的卫生间,可以洗澡。楼对面是有名的俄罗斯东正教大教堂(老百姓称喇嘛台),很是宏伟壮观。在东北局的这段时间,我们能看到画报,听到许多打仗的消息,学了一些战斗歌曲,如《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说打就打》等等。我知道蒋介石调动几百万大军打内战,还有美国的支持,可是被解放军打得节节败退。长春被我军包围,画报上一条毒蛇盘在一个桩子上,下面全是汪洋大海。我懂得这是说,长春的敌人已经被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包围,走投无路了。
在哈尔滨后来有一段时间,我们和妈妈住在一个工厂里,院里是堆积如山的大豆,地址在松花江边,我第一次看到美丽的松花江。可是,附近许多楼房都成了废墟,听说是日军731部队搞细菌战,使这里流行鼠疫,好多人家都死光了,只留下残垣断壁。
后来,我们又跟着爸爸到通化。1948年除夕,爸爸又奉命打点行装准备启程。我们的新旅途就这样又开始了。不过,已经不再是逃难,也不是撤退,而是向着新中国前进。大年初一早上,朝阳照耀着大地,我们一行人登上卡车准备离开这个青山绿水的小城。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爸爸奉命去接收沈阳。迎着灿烂的朝阳,我们的大卡车出发了。
(来源:《百年潮》2025年第5期)
Copyright @2014-2026 www.hbdsw.org.cn All Rights Reserved
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版权所有,未经书面授权禁止使用
技术支持:荆楚网 鄂ICP备18025488号-1


微信公众号

手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