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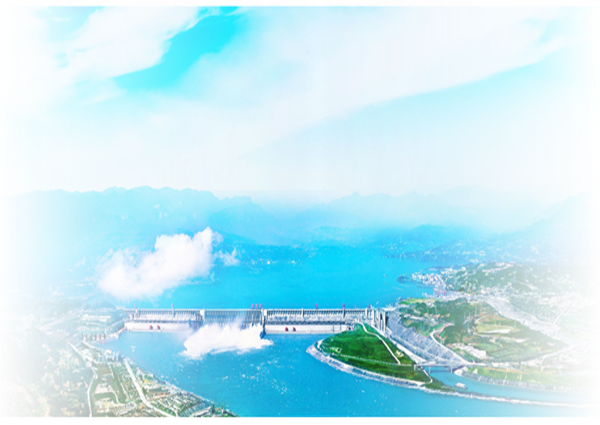
周良书
治学一般有两个途径:一是平时注意收集和积累资料,等到资料富足,便可就资料集中的问题撰写文章;二是先确定一个题目,然后围绕题目来收集资料,一旦资料比较齐备,即动手写作。古人治学大多采取前一种途径,主张以读书为本,在读书过程中不断积累资料,然后著书立说。现代学术更多体现的是工业生产的特点,需要定期定量地创造学术产品,以适应各类考核的要求,中共党史研究也不例外,于是围绕选题而读书写作,就自然要成为许多党史研究者成长成才的一种必由之路。
一、党史研究须过选题关
古人常说治学如串铜钱,片段的知识,好像一个个散钱,须用绳子把它们串起来。一个好的选题,就好比一根有用的绳子,它可以使我们所积累的知识条理清晰。这一点对于党史初学者来说尤为重要。事实上,许多有成就的学者,往往都是从选题开始,然后围绕它展开系统的学术训练,从而获得读书治学的“第一桶金”。
1.作好治学的第一个题目
吕思勉说:“世界上有许多事,是不能有所谓‘等一等’的。好像住房子,我们不能因好的没有造成,暂时等一年半年,这是不可能的。在新房子未完工前,简陋一黏的茅草屋,也是必要的。”这是极中肯的话,说明学问须从一个个具体的题目做起。但是我们心里也要明白每一个题目具体的价值和意义。否则,虽长了一头好发,结果却很难梳出几条像样的辫子来。这也就是说,研究者在起步前,还需做一些必要的准备工作。
一是要慎选题。一般文章选题需要慎重,研究生学位论文更是如此。因学习时间有限,而论文完成有期,因此选题一定要有所限制。有不少研究生目标远大,但在规定时限内却又无法完成,于是只好不断地压缩内容,而先前定下的题目又舍不得放弃,结果往往给人文不对题的印象。这的确是许多党史学位论文的通病,也常常成为匿名评审专家或答辩委员会成员所挑剔的地方。此外,选题还应当把知识、观点和材料统一起来。郑天挺曾有一句经验之谈,他说:“研究历史,要多问几个为什么。问的越多,解决问题越彻底。应当一个问题扣一个问题地追问下去,找到问题的根本性原 因和规律。”例如,研究“中国民主革命”这个题目,实际上就可分解为一系列相互关联的问题,诸如 “为什么革命”、“谁来革命”、“革谁的命”、“哪个先革哪个后革”、“革了命以后怎么办”等问题,甚至包括“革命”观念的由来等等。这些问题指示着研究的方向,并规定着研究的重点。
当然,研究者也不仅要问“题目”,而且还要问“自己”,以防止钻进牛角尖,走入死胡同。反问自己可能有几种结果:第一,被问倒了,后面留下一个大窟窿,这就要赶紧放弃,不要舍不得回头。第二,问的结果,总体上正确,但确实有漏洞,这就要坚持自己的观点,并且尽全力把漏洞补上。第三,各种反问,都得到合理解释,而且也能估计到读者可能提出的疑问和责难,这是最好的结果。只有把 3 种情况都考虑到,所选的题目才不会有大错。
二是要起好名。从作者方面说,有了题目,可以明确自己所写的中心。从读者方面说,看了题目,可以预知文章所含的内容。为选题命名的目的也就在于此。从前有截取篇首几个字作题名,比如第一句是“学而时习之”,就命名为《学而》;有人作诗,意境扑朔迷离,自己也捉摸不定,于是干脆就用《无题》作为题目。这在古人是常有的事,我们今天不可以这样做。命名主要还是根据所撰写的文章题材、材料基础、发表去向等情况来确定,题目本身则既要尽可能简洁明快,但又要使读者明白你阐述的问题所在。当然,学位论文题目字数可能会多一些,但也要以不超过 25 字为宜。
为选题命名有许多学问,它体现的是研究者的学养和功力。初学者在不得其要领前,不妨参照一下前辈学者的文章题目。比如张静如先生的《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纲》(《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2期)《个体的独特作用和群体的合力作用》(《党史研究与教学》2008 年第 4 期),就是很好的范例。此外,现在的学者也常用一些短语作为文章正题,而把要写的具体内容用副题表现出来,比如郭若平的《多重阐释: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五四”观念演进之“路线图”》(《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5期)、侯且岸的《思想革命:对五四运动本质和意义的省思》(《北京党史》2009年第3期);也有用并列词汇作为正题突出文章论述对象的特点,然后再把具体写作内容用副题表现出来,比如左玉河的《求真与致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双重品格》(《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5期)、韩钢的《考证与分析:毛泽东晚年的“两件事”谈话》(《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 3 期);还有用正题直接表达论述内容,用副题对正题作适度限制,比如郭若平的《“鲁迅风波”:当代中国思想史的一个侧面》(《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3期)、张海荣的《“苏联老大哥”形象的乡村建构(1949—1956)——以河北省若干县域为中心的考察》(《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5期)。这些我们也可以学习和效法。但是,也有人喜欢用“试论”、“述论”一类字眼命题,这不是说不可以,但总给人以“美中不足”的印象。
总之,治学的第一个题目,我们要尽可能考虑周全一点。这是读书治学的开端,因而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它可能还不是一道丰盛的午餐或晚宴,但也要色香味俱全。最要紧的是,米饭应该是煮熟的,否则吃夹生饭就更不好了。
2.尽量在“富矿区”找题目
《红楼梦》中,贾琏向鸳鸯借钱时说过一句话:宁撞金钟一下,不敲破鼓三千。有志于学者也应当多撞金钟,少敲破鼓。严耕望在《治史三书》中也强调这一点,即选题的范围要大一些,这里面可以包括许多小问题,“如此研究,似慢实快,能产生大而且精的成绩”。也就是说,选择论题一定要着眼于“富矿区”。可以先确定一个较大的领域,然后对所涉基本知识、研究现状和资料情况作一番考察,为开展专深研究奠定基础。最后再逐步缩小范围,聚焦于其中的某个问题,这样选题也就形成了。这是一种“农村包围城市”的选题策略。依照这种路径,研究者可以做到进退自如。如果某个问题无法研究,还可转到本领域的其他问题;在完成一个题目以后,也能够很自然地过渡到相关的问题。具体到党史研究,这种“富矿区”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
一是思想史上的“大人物”。历史无非是历史主体从事生产、进行生活的真实记录。而这种“记录”也不是某种凌驾于人、社会、历史之上的“创世结构”,它只有存在于社会历史之中并通过人才能表现出来。所以,史学研究的第一对象是对历史活动主体的研究,并且在研究“第一对象”中,还应当遵照从特殊到一般的认识规律。马克思说:“人的个人生活和类生活并不是各不相同的,尽管个人生活的存在方式必然是类生活的较为特殊的或者较为普遍的方式,而类生活必然是较为特殊的或者较为普遍的个人生活。”马克思道出了“个人生活”与“类生活”的辩证关系。一方面,“个人”代表着“类”的总体性,每个人都包含着“类”的一般性质;另一方面,“类”又是通过个人的个体形态来折射出自身的一般规定性。
其实,在历史上确有许多伟大人物可作某个时代的政治中心,有许多伟大人物可作某种学说的思想中心,这类人物也最宜于作历史研究的中心。梁启超说:“每一时代中须寻出代表的人物,把种种有关的事变都归纳到他身上。一方面看时势及环境如何影响到他的行为,一方面看他的行为又如何使时势及环境变化。在政治上有大影响的人如此,在学术界开新发明的人亦然。”在中共党史上,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邓小平就属于这一类人物,找到他们也就找到了党史研究的“富矿 区”。从他们的思想可反观一类人的思想,从他们的实践也可反观一类人的实践,进而又可从这一类人的思想和实践来揭示丰富多彩、波澜壮阔的中共历史的全貌。
二是事件史上的“大关节”。中共历史发展既有由量到量的渐进性变迁,也有由量到质的飞跃性转折。其中,飞跃性的转折是历史发展中的一种特殊状态,即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党的实践活动方式出现整体性和根本性的变更趋势,它在中共党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我们可以用莱布尼茨提出并在后来又得到孔拉德·洛伦茨赞同的“闪光”术语来描述它。“闪光”即历史发展的加速期,它指的是在平常条件下需要多少年才能走完一个周期的各种发展过程,通过飞跃性转折而完成的那一段非常短暂的时期。我们也可称其为事件史上的“大关节”,这是历史发展过程中含“金”量最多的地方,也是各种矛盾运动十分激烈的时期。
比如,五四运动就具有这种“大关节”的特点。因为在其中,人们往往比平时更易于见到新旧事物之间冲突、转化、否定、互动的辩证本质。它犹如火山喷发,将历史中最内秘的东西贡献出来,使之暴露无遗。这也是长期以来历史学家乐此不疲的原因所在。并且,每个研究“现代中国”的学者, 都可以参与到建构“五四”的行列中。于是在中国学术史上遂出现大家都来说“五四”的繁荣场景。此外,中共党史上的一些重要会议,如中共“一大”、“七大”、“八大”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等,也属于事件史上的“大关节”。当然,还有一些会议,如西湖会议叫“中共中央特别会议”,八七会议叫“中共中央紧急会议”,遵义会议叫“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也同样值得关注。这种不一般的称谓,本身就蕴含着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内容。
在党史研究中,有人从思想史上的“大人物”入手,如张静如先生,后来成为国内李大钊研究的 “第一人”;也有人从事件史上的“大关节”入手,如彭明先生,后来成为国内五四运动研究的最知名学者。这都是从“富矿区”找题目,并取得研究成功的例证。
3.把握从选题到学问的环节
选题是决定研究成败的一个关键因素,但它毕竟还不是成熟的学问。研究者只有好的选题,若不“持之以恒”,不“触类旁通”,也只能“望题兴叹”,更不用说将来会有大的成就。这就是“行百里者半九十”的道理。因此,研究者在确立选题后,还需抓住以下几个必要的环节。
一是找准学术史定位。梁启超说:“人类活动好像一条很长的路,全部文化好像一个很高的山。吾人要知道自己的立足点、自己的责任,须得常常设法走上九百级的高山上添上一把土。因是之故,第一要知道文化遗产之多少。若不知而创作,那是白费气力。”这表明,研究者一定要事先找准 选题在知识系统中的“领域定位”,以明确其研究的学术价值。
我在先师张静如的指导下,选择高校党建史研究,就曾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首先,就党史研究的对象而言,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党治史”,一是“治党史”。但从研究的现状看,中共“治党史”研究还是个薄弱环节。而作为一个全国性大党,中共党建又涉及到企业、农村、学校、社区等各个方面。一部完整的党建史应是建立在以上各方面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的。因此,从这个角度说,开展本项研究,就可以丰富中共党建史乃至整个中共历史的研究。其次,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也是多年来学界关注的一个老话题。我的研究当然不是在一般意义上讨论这个问题,而是要在现代中 国的特殊时空下,具体地探讨中国学生与中国政党间的内在联系。因此,从这个角度说,开展本项研究,也许还可为政治学研究和教育学研究提供一个典型个案。张静如还对我说,这个题目“以往没有任何一个人研究过,研究出的成果完全是一种创新”。这对于我可以说是一种莫大的激励和鼓舞。否则,我也很难想象会有今天的这一点进步。
二是沉下身子做学问。钱穆曾慨叹:“近人求学多想走捷径,成大名。结果名是成了,学问却谈不上。比如五四运动时代的学生,现在都已成名,但问学术,有谁成熟了! 第二批,清华研究院的学生,当日有名师指导,成绩很好,但三十几岁都当了教授,生活一舒适,就完了,怎样能谈得上大成就!”在党史学界,这样的事例也不少。有的名师指导,选择好的论题,结果一举成名,但是却无以为继,致使学术难以成熟。这便是胡适之所说“暴得大名,不祥”的道理。
正因为此,钱穆一再告诫他的学生严耕望:“你将来必然要成名,只是时间问题。希望你成名后,要自己把持得住,不要失去重心。如能埋头苦学,迟些成名最好!”可见,对研究者来说,“成名”容易“成家”难,因为后者更须“沉下身子”,多一份“埋头苦学”。大画家黄宾虹说:“善撰文者常谓写文章不易,善做诗者常谓诗不易做,善作画者常谓画极难。此理所当然,若感到撰文,做诗,作画容易,便难进步矣! 遇难事如在深山遇虎豹,不能胆怯,要学武松,过得景阳冈,便可到家。”治学之道不也是如此吗?
三是经常抬头看看路。这是何兆武先生的话,他说:“当代实践的历史学家们往往习惯于‘低头拉车’而不习惯于‘抬头看路’。”在党史研究中,这种情况也比较常见。许多研究者满足于既定格式,在前进道路上不愿意或不善于作方向性调整。于是有了选题,似乎也就有了结论,研究者的任务无非就是要为这个结论,再补充上一份例证而已。若能补充一项例证,就算收获一份成绩;若能补充两项例证,就算收获两份成绩。这也是党史研究中难有创新性成果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向国外的研究者学习。在海外中国学研究中,美国学者费正清从“欧洲中心论”视角,提出“冲击——反应”的分析模式,强调西方对近代中国内部社会变革的主导作用。但他的学生保罗·柯文却不受其限制,主张“在中国发现历史”,形成了“中国中心观”的解释框架,要求关注在传统影响下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自身逻辑。而费正清的另一个学生——美籍华裔学者王国斌,则又反其道而行之,认为要超越“欧洲中心论”,就应首先回到欧洲,主张既从欧洲角度考察中国,也用中国标准评价欧洲,并将两种视角结合起来。他以此观察中国历史,也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总之,研究者在确立选题后,既要做“低头拉车”工作,更要经常“抬头看路”,这样才能把握好 读书治学的大方向。
Copyright @2014-2022 www.hbdsw.org.cn All Rights Reserved
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版权所有,未经书面授权禁止使用
技术支持:荆楚网 鄂ICP备18025488号-1


微信公众号

手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