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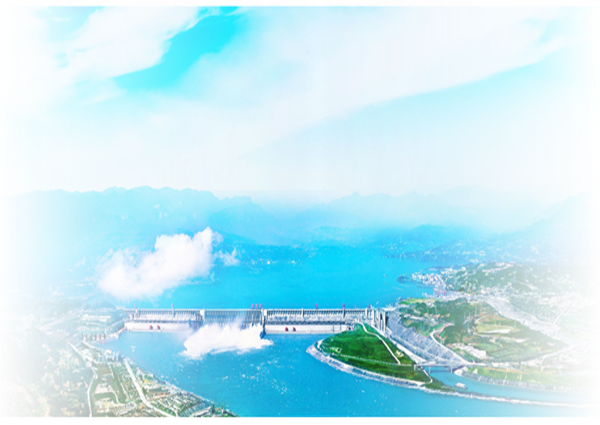
郑奇英
1925年,23岁的父亲郑位三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年我出生于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我们家是革命家庭,祖父郑维翰是乡苏维埃政府主席,并在县苏维埃做过财经工作;二叔郑植惠、四叔郑植棣、姑姑郑成香在土地革命时期就参加了革命工作。我母亲曹茂云是贫苦农民出身,她爱劳动,地里的活样样都会干。我父亲时常不在家,母亲认为我们这房人对家庭贡献小,因此只要她能干的活都抢先去干。在弟妹面前她是老大,特别尊重老人,关心弟妹的生活,参加妇女组织的活动也很积极。1933年冬,国民党占领我们家乡后,她“跑反”进山,躲藏在山洞里最后冻饿而死;这期间全家有4个人先后牺牲。
我的家乡在苏维埃时期,人民分得田地后生活慢慢好起来,村里的老百姓积极参加农协会、妇女协会、青年团、儿童团等组织,参加红军的人也很多。我四叔当时是儿童团的大队长,时常带我和他们一起出操、站岗放哨。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家乡后,国民党对根据地红军的家属“斩草除根”,我们家大人都“跑反”或上山打游击。七八岁的我在村里变成无依无靠的人,开始村里的好人留我吃住,到国民党建立保甲制后,村里人怕我连累他们就不敢留我吃住了。当时父亲任鄂东道委书记在鄂皖边区活动,后派人来接我。我们白天躲藏在老乡家内或山内,晚上赶路,走了好几天到卡房镇见到我父亲。这是母亲死后我第一次见到父亲,我伤心地哭了。父亲亲切地说:“奇英,你别哭,我会把你抚养成人,以后带你当小红军,红军里很多人会教你识字、教你做事。”父亲还对我说,红军是穷人的军队,是代表老百姓利益的;红军里的人都是受苦人,当官的不打当兵的;红军是打国民党反动派的。我过去只见过游击队便衣队,听了父亲的一番话后觉得当红军好,红军比游击队便衣队人多,不怕国民党。父亲还教育我要好好学文化,没有文化的人学不到真本事,没有文化的人只看到眼前的事,国内国外的大事都不知道;我们现在没有学校不能安心读书,有文化的人教你认字,一天学几个字,慢慢你就会看书看报了。
不久,父亲送我到红二十八军医院,学当看护员。院长熊德安同志是个坚强的女性,她立场坚定、工作负责、爱护伤员、关心群众,大家都很尊重她。那时我们医院条件很艰苦,伤员们有的住在山洞里,有的住在草棚里;医药用品都很医乏,主要是靠便衣队找关系从敌占区买,绷带和纱布换下来用开水煮过后再用。我每天主要是洗绷带、纱布,学习给伤员换药。看护长戴醒群同志是张体学同志的夫人,每天教我五个字,没有纸就在地上写,我边工作边学习,半年后我慢慢会写简单的日记和记流水账了。可惜的是戴醒群同志在抗战时牺牲了。
1937年,第二次国共合作前,国民党企图消灭红二十八军,派大批军队来清剿我们,医院被包围,院长熊德安、看护长戴醒群和大部分医生、护士、伤员被敌人抓住了,我也是其中之一。敌人把我们押到经扶县(今河南省新县)关起来,在敌人审问我时,我只说我叫李梅英,父母双亡,前几天讨饭到这里,红军把我留下了。每天敌人审问我就是这几句话,当时我心里明白,父亲是红军的“官”,如暴露了国民党不会放过我。事后,别人都说我懂事,骗过了敌人。在敌人的牢中每天只有两顿稀饭,戴醒群左臂负伤不能动,我给她送饭,照顾她。
父亲离开红二十八军后,我一直在红二十八军医院工作。这段时间从院长、医生到护士对我都很好,照顾我生活,向我传授护理知识,教我学习文化,便衣队从敌占区带点什么好东西总是有我一份。熊院长还带我认红二十八军政委高敬亭做干爹。高敬亭对我说,你父亲不在这里时你就是我的女儿,医院里哪个对你不好我就批评他。高军长对我确实很好,每次见到我都把我抱在怀里,问寒问暖,问我吃饱饭没有,学习文化没有。我对他也很热情,每次看见他都大声地叫他干爹,愿意亲近他,他可高兴啦。我从经扶县出狱后,他还特意把我接到他身边住了一段时间,心疼我在敌人牢房里吃了很多苦。那时他与史玉清已经结婚,干爹干妈对我都很好,经常带我去他们小灶吃饭,对我疼爱有加。我父亲抗战初期从延安重返大别山鄂豫皖根据地后,我们关系还一直很好。父亲曾多次向高敬亭夫妇表示,感谢他们对自己女儿的关心照顾。我们的关系直到高敬亭同志被错杀后才不得不终断。
在鄂豫皖地区,由于高敬亭和部分干部、战士对国内外新形势认识不清,对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重要意义认识不够,思想不通,认为国共合作是向国民党“投降”。党中央派我父亲、程启文、肖望东、张体学等同志来做工作。父亲等人通过形势教育,宣传国共合作的意义,进行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逐渐使所有的干部、战士提高了思想觉悟,认识到大敌当前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意义。后来红二十八军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下辖五个团,还有兵站、留守处,驻防在黄安县七里坪一带。不久开赴抗日前线。
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肖望东与国民党谈判成功,国民党释放了关押的红二十军人员,程启文同志接我出狱。但国民党不讲诚意,在谈判过程中他们还是杀害了我们七八个领导同志,如一位姓张的参谋长,熊德安院长等。出来的同志有的回家了,大部分同志都回到部队,戴醒群和我回部队到新四军四支队留守处医院继续工作。在七里坪我见到了日思夜想的父亲,父亲抚摸着我的头欣慰地说:你被国民党抓去坐牢,受了苦,现在能回到我的身边我很高兴。我告诉父亲我改姓名骗过敌人的事,并说好多认识我的人都没有向敌人告密,如要是有人告密我就不能活着回来。父亲听后拉着我的手夸我聪明,有胆量,并说有那么多叔叔阿姨保护过你,你永远不要忘记他们,有机会要感谢和报答他们。我点点头说我会永远记住他们的。父亲还关切地问我挨打没有?我说国民党当兵的用枪托打我,我跌倒了,门牙磕到石头上,把两个门牙磕掉了,牙根还发炎流脓,现在好了。父亲心痛地看了我的伤。他告诉我日本侵占了我们中国很多地方,不打日本就要亡国。现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你在医院要好好学习好好工作,等以后抗日根据地有学校就送你去读书。
1941年,父亲任新四军二师政委,在淮南抗日根据地建立了一所联合中学,父亲才如愿以偿地把我送去读书。中学校长王昭诊是共产党员、大学生。我们班主任刘加林在政治上很关心我,还是我人党的介绍人。学校老师中多数不是党员,他们都是城市里的知识分子,来新四军参加革命的进步青年。我因没有上过小学,学习基础不好,特别是数学有些跟不上;但在政治上我比别人强,下乡宣传抗日我是宣传队长,演出节目我是主角。可惜我在联合中学只读了两年书,1943年秋,父亲调新四军五师,把我带走了。
父亲到五师工作后不久,有一次对我说,你文化水平有了些进步和提高,但还不够,今后还要努力学习。另外,要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和革命战士,光有朴素的阶级觉悟还不够,还要有政治理论水平。随后父亲把我送到五师办的党校学习,通过半年多刻苦学习,不仅使我在政治理论上有所提高,在文化上又有新的进步。我觉得自己真正长大了,道理懂得多了,工作做得更好了。父亲对我的要求越来越严格,虽然他工作很忙,每次见到我时都要我向他汇报自己的工作、学习情况,有什么做得不好的地方,他总是耐心地批评教育我。父亲为了锻炼我,又叫我随部队到农村工作了半年。
1945年初,组织上分配我到司令部机要科当机要员,我们主要是负责五师与新四军总部的机要通讯联系工作。同年10月底,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原军区成立,父亲任中原局代理书记兼中原军区政委,他的工作更忙了,我们父女见面的机会就更少了。1946年夏,国民党蒋介石调动几十万军队围攻中原部队,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父亲和先念同志的正确指挥下,中原部队全体指战员不怕牺牲,克服各种困难,突破敌军重重包围,转战千里,胜利完成了党中央部署的战略转移任务。
我,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在部队这个革命大熔炉里,在父亲无微不至的呵护下,在熊德安院长、戴醒群看护长、高敬亭干爹和很多叔叔阿姨及同志们的关心、帮助、照顾、爱护下,成长为一名革命战士,能为革命事业、党和人民做了一点工作,我感到无比的欣慰。这都要万分感激我的父亲带我当红军。
在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中,父亲对人民忠心耿耿,同敌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历任党政军重要领导职务,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革命事业贡献出了自己的一生,他的名字将永远被人民所铭记。
我永远深深地怀念敬爱的父亲。
(选自《我们的父母》一书)
Copyright @2014-2022 www.hbdsw.org.cn All Rights Reserved
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版权所有,未经书面授权禁止使用
技术支持:荆楚网 鄂ICP备18025488号-1


微信公众号

手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