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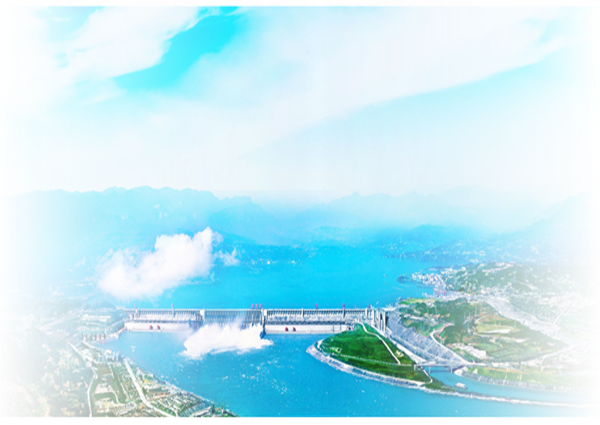
余 玮
周恩来在兄弟3人中是老大,大弟周恩溥,小弟周恩寿。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原委员、中国新闻社原副社长周秉德是周恩寿的长女。她的少年和青年时期,曾跟随伯父周恩来和伯母邓颖超共同生活了15年之久。
一个中午,记者如约走进一套老式红砖公寓。精神挺好的周秉德谈起在中南海度过的难忘岁月,谈起伯父伯母对自己的关怀与体贴及教诲,显得那么的激动与忘情,时而激昂,时而沉思,恍然回到了西花厅岁月。
第一次见面,伯父边端详边寒暄
1937年4月,我在哈尔滨降生,这着实让三代没有姑奶奶的周家上下很是兴奋了一阵子。1943年全家投奔天津的四奶奶,在天津我念了小学六年。
在我小学三年级的一天,爸爸在翻阅《益世报》时,看到有关大伯的消息,很是兴奋,悄悄对我说:“你伯父在共产党内是做大事的。”从这,我便晓得自己有一个是共产党大官的伯父周恩来,也盼望有那么一天能很快见个面道个好。
1949年上半年,已在北平华北革命大学学习的爸爸,在同伯父的一次谈话中提到,女儿秉德小学毕业在即,想接她到北平念中学。伯父知道我爸爸在革大住的是集体宿舍,带孩子不方便,便提出让侄女住到自己的住处来。
那年6月下旬的一天,刚刚小学毕业的我在火车的汽笛声中告别了天津,告别了妈妈与弟妹,随爸爸来到了北平。一位清瘦精干的叔叔领我进了中南海。进门,绕湖,再进门,不多时我被带到了一个叫丰泽园的院子里,那是四合院式的平房。我当时说不上激动或高兴,只觉得新鲜,自己在院子转来转去。
只一小会儿,在外边开会的伯父回来了。他高大魁梧,脸庞丰满红润,与爸爸有点像,也有两道浓黑的剑眉。见到我,他亲热地拉到他身边,左右端详,笑着说:“呦,你好像你爸爸,又有点像你妈妈。”
问了我妈妈及弟妹的近况后,又寒暄了许久,伯父才吩咐卫士安顿我的住处。我被安排住在一排坐南朝北的房子里,住在西边,屋里有几个书柜,东边一间是伯父秘书夫妇的住房兼办公室。房子的条件比我家里要好,但绝不豪华。
当时,伯母不在,她受毛泽东主席之嘱,到上海接宋庆龄先生去了——迎接她来北平共商建立人民共和国大计。8月28日,我随伯父到北京站去接伯母。火车站里锣鼓喧天,伯父和其他党政领导人都走到前面去与宋庆龄先生握手交谈。“你就是小秉德吧!你好!”叔叔把夹在人群中的我领到伯母面前,伯母便握住我的手笑吟吟地说。我随即向伯母问好。这是我第一次与伯母相见,那情景至今常常浮现在眼前。
伯父、伯母一生无儿无女,多年来一直把自己对儿女辈的感情全部倾注在一批烈士子女身上。亲侄女来到身边,自然疼爱万分,把我看成女儿一样,我也很快适应了在中南海的生活,感受到在北平也有一个充满亲情而温暖的家。
我住在书房里,有许多我从未见过的书。“你住的是间书房,可以在那多看些书。毛泽东伯伯就住在前面,他工作忙,不要去打扰他。”伯父的话,我现在还记得。我常常一个人坐在伯父书房里看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李有才板话》等等好多书都是在那时期看的。
平时我不是经常能见到伯伯,因为他夜里办公,一般只在上午睡上几小时。白天里,小院常常静得很,除了鸟叫还是鸟叫。看完书后,我往往呆呆地望着高处,思念在天津的开心时光。还好,不多时,认识了李敏、李讷等好多小伙伴,我们或一起看书,或一起唱歌、玩耍、聊天。这时,我才真正适应了中南海的生活。
一件件小事中,我看到了一个伟大而崇高的伯父
那一年秋天,我顺利地考上了北京师大女附中(现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进了干部子弟班就读。平时住校,每个周末回家看伯父、伯母,向他们兴致勃勃地讲学校里的事。有一回,伯父听了对我讲:“你们班是干部子弟班,革命老区来的孩子多,他们身上有许多革命老区传统,你要努力向他们学习,向他们看齐。”
卫士叔叔见我从天津来时穿的两身小花衣裙在秋季穿显得单薄了,便骑自行车带我到王府井订做了两套秋天穿的衣裤。没多时,第一套兰色咔叽布小西套装完工了,穿上真精神。吃饭时,伯父看见了,说:“不错!哪里来的?”我如实回答:“叔叔带我去做的。”几天后,我又换上了另一套黄咔叽布的衣裤,这下伯父看见后便皱了皱眉:“怎么又做了一套?浪费!”原来,当时实行的是供给制,伯父嫌我做多了,多花了公家的经费。
不论伯母怎样解释“秉德住校,得要有两身衣服换洗”,伯父却谈起了自己的住校史:“我在南开上中学,夏天就一件单布长衫,冬天也就一件藏青棉袍,周六回去就洗净晾干。现在国家还困难,我们还是要节省嘛。”我那时并不太懂,但还是使劲地点头,认定伯父说的话一定对,照着办没错。
每逢周六晚上,春藕斋开舞会,我们孩子也跑进去玩。才学会一点“舞”艺的我们,看许多姑娘排着队等候与伯父等好些中央首长跳舞,于是也壮着胆子下舞池。我伯父的舞姿很棒,风度翩翩,舞步流畅,舞姿优雅,只要他一到场,几乎再没办法在场外落座。好不容易轮上我同他跳,伯父微笑着揽住我的背,踩着音乐步入舞池。“跳得还行,你乐感可以。”听到伯父的夸奖,我不免有点飘飘然,不料他又说了一句,“转到那边你就下去吧,让别的同志跟我跳,看好多人在排队”。觉得不太过瘾的我,无奈地点头。这就是我的伯父,宁可委屈亲人也不愿让他人失望。
1949年11月,我随伯父、伯母搬进了中南海最西北端的西花厅。那时,我妈妈与弟妹也来到了北京,我与大弟秉钧、大妹秉宜一同住在西花厅的东厢房里,三张床并排着,彼此中间留点活动小空间。因为北面挨着的是伯父的卧室,他夜里办公、上午睡觉,所以我们在室内不敢嬉戏与大声说话。
有一回,爸爸提出把大妹过继给伯父,伯父却另有想法:“如果我要了这个孩子,别的孩子就会认为我这个做伯父的不公平。再说,她也会养成特殊化心理,对她的成长没好处。”伯父总是想得很周全。
弟妹在北京八一学校读书,学校里的同学家庭条件稍好的便会有车接送,军区里的孩子坐单位面包车。弟妹上学放学是卫士叔叔骑一辆三轮车接送,尽管伯父、伯母都有车,但从未为我们使用过。“车是工作用的,小孩不应该享受,你们从小不要依赖家庭关系,不要奢求非分享受,要自己奋斗,要自律自立。”伯父时常给我们如是讲。
Copyright @2014-2022 www.hbdsw.org.cn All Rights Reserved
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版权所有,未经书面授权禁止使用
技术支持:荆楚网 鄂ICP备18025488号-1


微信公众号

手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