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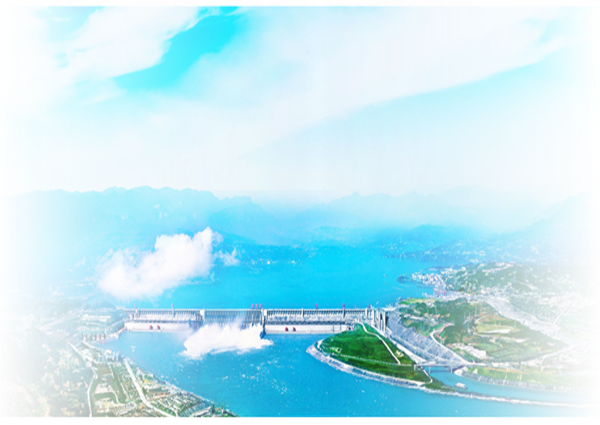
黄火青
1927年4月间,中共枣阳县委派我到武汉投考工人运动讲习所。讲习所的“考试”很有意思,负责考试的同志事先让我们集中住在汉口友益街尚德里团市委的房子里,然后悄悄将考题告诉我们,嘱咐我们能写文章的同志自己写,不会写的就请人帮忙。但到考场时不要露了馅,让人家看出你已在下面打好稿了。接着,安慰我们说:你们有组织介绍信,考试管理和最后审定都是我们的人,大家一定能考上。作好准备后,就在德国中学(即球场街现市六中所在地)进行“考试”。考过后,分了两个所,我在一所,对外叫工人运动讲习所,实际是培养县区党团干部的。地址在汉口黄陂会馆,所长是许子桢,学习时间为三个月;二所设在德国中学。大概是5月下旬,汉口血花世界里正在召开太平洋劳动大会,我们全体学员列席了会议,作为我们的开学典礼。
那时我妹妹黄海明是武汉工人纠察队训练班的队长。开会时,她正带着人在外面站岗。会上,我们看到了刘少奇同志,那时他还是个风度翩翩的青年,身着西装,一个手指头那么一指一指地讲话,他后来说话还是这个姿势。
开了学,课还来不及上时,突然传来了驻宜昌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叛变的消息,其前锋已犯武昌纸坊,进逼武汉。当时武汉政府掌握的军队大部分开抵河南二次北伐去了,后方极为空虚,形势异常危急。武汉国民政府中央临时决定将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学生编成一个独立师(侯连瀛任师长,恽代英任党代表,施存统任政治部主任),会同农讲所的学生,由当时独立二十四师师长、武昌警备区司令叶挺统一指挥,开赴纸坊迎敌。
一天,我们刚吃完晚饭就立即集合。正在大家纳闷的时候,市委组织部魏部长来了,他是个小矮个儿,法国留学生,西装领带,挺神气的。他对我们讲,因为形势很紧张,市委决定除了妇女和小孩外,动员大家全部参军。这一下可炸了锅,男同志眉开眼笑,女同志急得又哭又闹,有个叫张玉珍的女同志,闹得非常凶。我妹妹海明也一下子跳到了主席台上,痛哭流涕地放了一通炮。说革命要讲男女平等,为什么男人能当兵,女的就不行!十五六岁的童子团也跟着起哄,说:“不要我们革命呀,谁不要我们去,谁是反革命。”这下子不好收场。于是决定“都去!”大家才破涕为笑。
当晚我们乘月色从汉口出发,街上童子团几十步一岗,手持棍棒维持秩序。我们一直被带到武昌胭脂山,省委当时就在山上。然后到达粮道街啸楼巷上的一个地坪上待命。记得当时陈潭秋跟我们讲了话。赶了几十里路,大家又困又饿。这时有人送来了槽子糕,就是鸡蛋糕,每人两块,喝了一点水,才觉得好些了。几小时后,我们又被带到司门口,再去平湖门,那地方老地名叫“老骑兵团”,是个军营,我们就在那儿住下了。随即与那儿的一部分人汇合,作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一个补充单位,它是中央独立师,我们就叫它补充第二营。在我们隔壁一个土院子里住的是第一营,是从广东来的农民自卫军。我们二营有两个男兵连,一个女兵和娃娃连。我在男兵二连当兵,妹妹是女兵娃娃连的连长。因形势紧张,恐被人窥出虚实,我们趁夜悄悄地开进独立师的空房,并派了岗哨,虚张声势,装出独立师没有走的样子。
有一次,我们在两湖书院集合,那儿也是武汉军校的驻地。我们坐在墙边的一个走道里,听了周恩来同志的讲话,他是上海暴动后来汉的;还有一个叫尹宽的也讲了话。我们参军就是为了打夏斗寅的。当时大家准备了水壶、水杯、背带等东西,非常急切地盼着上前线。可是等了几天,却说夏斗寅已被打垮,不需要我们去了,要我们仍在补充二营当兵,留守武汉军校。记得我们还发过一次饷,七元五角六分钱,都买莲子吃了。还有青龙巷的牛肉豆丝,又便宜,又解馋,一有钱我们就去吃一碗。我们营长叫刘自志,湖南人,黄埔三期学生,后来上井冈山了。连长是上海人,立三路线时还在,以后就不知下落了。排长黄魁,湖南人。我们二连的党团员占百分之九十,一连是百分之八十五。我们平常在新兵营也闹些意见,认为地方派我们来是接受干部训练的,不是来当兵的,七七八八地不安心。那时恽代英是军校的实际负责人,凡是有人闹情绪的时候他就来了。有人闹意见,出现反映,他就集合大家讲话。他很会说话,说完后还问大家有什么意见,没意见了,“好”,散队。
那些日子够紧张的,每天天亮下早操,然后吃早饭,两碗稀饭,两个小馒头,一点辣子、一点黄豆、再一点紫菜。我们都是坐着的,一听“开动”,就赶紧喝稀饭,一片“呼啦呼啦”的声音。大约四五分钟时间,值日排长哨子一吹,一声“立正”,就不准吃了,得立即排队。大家都抓起两个小馒头跑,排队时吃,不然吃不饱。时当夏天,天天都打野外,队伍往洪山跑,有时到珞珈山,天热路远,爬上滚下,硬是一个多月没有洗个痛快澡,汗臭味特别难闻。女兵就更辛苦了,也是同男同志一样打野外,记得有个叫周玉珍的,河南人,跟不上队,不要她去她不干,去了又掉队,掉队就关禁闭,等我们下操,她还在哭鼻子。操练中是没有男女区别对待的。说要下水,男的女的都得往下跳从水里上来,有些女同志身上被擦伤,鼻子口里都是血。晚上睡觉也不安稳,有时来个紧急集合。打绑腿可成个大负担,睡觉时就不解开,值日的查出来算犯纪律,解开又怕集合时绑不赢。于是先睡一会儿,等查过了铺再起来悄悄打好,一声令下就集合。情况紧张的时候,就传令“今晚不准解绑腿,子弹袋不准下身子,就这样睡觉,有紧急事马上起来”。的确是枕戈待旦。有天晚上,我们饭堂里“叭”地响了一声,好家伙,把大家都惊醒了,一个个都跳起来,抓起枪,准备战斗。这时连长喊道:“你们干什么啊?敌人在哪儿啦?”一查看,才发现是饭堂的灯泡炸了,受了一场虚惊。
我们新兵营每天下早操,打野外,上政治课,学《步兵操典》和军事理论,紧张地生活了一个多月,直到6月底迎接军校学生凯旋归来,取消中央独立师名义,才返回军校学习。当时国共两党关系日益恶化,共产国际来了一个指示,要求中央迅速武装五万工农。于是中央军校决定选派一批人去苏联学习,培养军队干部。当时各单位都派了人去,我们新兵补充二营选出了七十多人,我和妹妹都选上了。大概也是6月底,我们先去上海,然后坐船去哈尔滨,再到苏联。我进了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特别军事政治训练班,实际由共产国际东方部管理,妹妹进了东方大学。我们走后,新兵补充二营编入了中央警卫团卢德铭部。
(摘自《湖北文史》2001年第4期)
Copyright @2014-2022 www.hbdsw.org.cn All Rights Reserved
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版权所有,未经书面授权禁止使用
技术支持:荆楚网 鄂ICP备18025488号-1


微信公众号

手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