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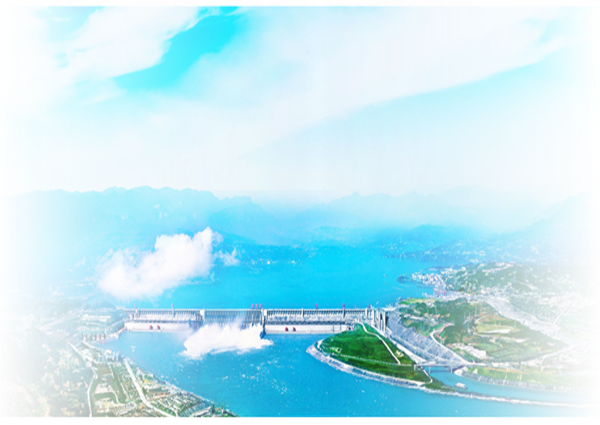
李 锐
校园里有不少怀着满腔忧国之情的学生
“一二·九运动”前后,我在武汉大学工学院读书,参加过当年武汉的学生运动。
1934年高中毕业后,我与文立徵、秦本立等三个要好的同学上北平升学,向往故都学生的“自由生活”,决心再也不回长沙了。他们都在平津入学,唯独我考入武大而南归。
那时,华北形势已渐危急。1933年5月,《塘沽协定》签订之后,蒋介石连“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调子也不唱了,完全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进逼,使冀察两省门户洞开。关心时局,不满意蒋介石政权的青年学生,自然怀着满腔忧国之情。
武汉大学的前身是湖北自强学堂,民国建立后改为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1928年秋改为国立武汉大学。胡适、蒋梦麟等投靠蒋介石政权之后,学校班底由《独立评论》派的一些人物组成,王世杰任校长。校址原在城内东厂口高师旧址。20世纪30年代初,在东湖珞珈山修建了宫殿式新校舍,这是一个美国建筑师仿照承德有名的八大处格局设计的。王世杰吹嘘,武大学生所摊费用在全国标准最高。王任教育部长后,由王星拱接任校长。珞珈山湖山秀丽,校舍堂皇;可是空气沉闷,死水一潭。我和新结识的几个湖南同学,晚饭后常散步湖边,议论人生,感慨时局。
“一二·九运动”以前,学校中活跃的是右派学生,而不是左派。国民党的复兴社是1932年成立的。大概就在这一年,武大文法学院的学生中就有了这个组织的成员。他们后来有一个外围组织——动力社,以读书会友相标榜。这些复兴社分子有的可能有“活动费”,于是在人们眼中立即出现这种标志:换一身西装,忙着找爱人。其中有的人功课尚好,甚至在同学中有一定声望,但多数是为混一官半职的中下之流。在国民党的血腥统治下,20世纪30年代初的武汉,十里洋场,一片荒漠。学校中少数思想左倾的学生,多是“单干户”,只能偷偷读书,赋诗言志;或者组织读书小组,交谈心得。图书馆可以借到英文或日文的马列著作,如《国家与革命》《资本论》等,也有考茨基、托洛茨基的小册子。如陈宽(陈家康,经济系)、吴月缸、刘佛年(哲学教育系)、杨克穆(杨作材,法律系)、黄美健等,就参加过这样的小组,他们都是1929年考入预科的,当时自称“闭门读禁书”。复兴社分子曾猖狂一时。吴月缸、陈宽都因思想激进,受到复兴社分子的威胁,于1933年先后被迫离校,到上海去了。陈宽的好友、外文系的叶君健只好作“隐士”,除跟同系好友谢文耀、林守正往来之外,再也不敢在人前谈心了。
1934年冬,为了打破学校生活的沉寂,我与魏泽同、王前等几个湖南同学作过一次失败的尝试:想成立学生会。那时校中的学生组织只有大大小小松散的同乡会,以湖南同乡会人数最多。我们是Freshman(新生),办这类事还得仰仗高年级有“威信”的人。可是我们找到的湖南同乡会负责人,却是复兴社分子许升阶。许读政治系,比我们高两班,是魏、王的中学同学,当时我们还不知道他是复兴社分子。我们联络了几十人贴出大字报,主张以同乡会为基础,组织全校学生会。学校原有管理学生生活的斋代表(男生宿舍共十六斋,以天、地、玄、黄等为斋名),后来以斋代表会名义召开的全体学生大会上,选出许升阶等7人为执行委员。除了复兴社外,学生中还有CC分子、国家主义派等。许升阶遭到上述这些分子尤其是思想进步的同学的反对。反对最力的有许的同班同学谢远达(谢抗战时在晋察冀边区工作),他们当然知道许的复兴社身份。反对者联名贴出大字报,说选举不合法,要成立学生会得先起草章程,产生班代表,由班代表会选举负责人。由于临近寒假,我们贴出大字报,说明年再说。学生会成立不起来,我与魏等反被进步同学怀疑为许某一伙。
这时的形势同20世纪30年代初已大不相同,一般说,并不很缺乏进步书刊。如《新生》《世界知识》《读书生活》等杂志和《大众哲学》、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以及《青年自学丛书》等小册子很多,天津《益世报》常有较好的社论。左倾学生爱好文艺的多,尤好读鲁迅的书。工学院虽然功课很重,我却爱读课外书。总之,国难当头,苦闷之至。
除开读进步书刊、同朋友漫谈之外,最有兴趣的事便是跟文立徵通信。文在辅仁大学化学系。我们大体每周一信,无所不谈,当然常议论华北局势。1937年5月,在抗日战争爆发的前夕,文立徵毅然退学,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后当过有名的铁道游击队的政委。1945年2月22日,在鲁南牺牲。
北平“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传来
1935年12月9日,北平爱国学生6000余人,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北平“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一传来,同学们议论纷纷,但报纸上的报道很简单。过了几天,我收到文立徵的长信。他参加了这天的游行,详细描述了游行队伍在北平王府井南口同警察的水龙奋战的情景。这封信在同学中传看。当夜,我用大张报纸抄写好,第二天一早贴在文学院门口;还找来一把旧菜刀置于墙沿,另纸书明:谁若撕毁,当以汉奸论。当时文学院兼作学校当局的办公楼,人们来往多经此处。这就如同一锅热水,加了一把猛火,立刻开锅了:同学们更加情绪激昂,商谈如何响应北平学生的行动。珞珈山远在武昌城外,同三镇学校素无联系,校内又没有统一的学生组织,这时只有各班内部和班级之间的熟人相互串联。工学院有机械、土木二系(1936年才有电机系),同学比较单纯,没有复兴社等类分子。我的同班石秀夫(刘清)、郭佩珊以及土木系的鲍光华等,原是平津来的学生,汤钦训、李昇震等原和我中学同班,两系中球员又多(我与石、汤、李等都参加球队),平时都很合得来,于是两班五六十个同学一起开会,商议行动的办法。魏泽同、周纪发、王前、彭秉朴、刘锡尧(刘西尧)、张仲翥等一批湖南同学和潘乃斌(潘琪)、钱祝华等一批江、浙同学,在文、法、理学院同时活动。在饭厅议论时,张仲翥感情激动,号啕大哭。所有各系的爱国同学都积极行动起来了。头一件大事便是商议如何召开全校学生大会,一致行动,并同山下三镇的各校学生取得联系。
为了争取教授和学校当局的同情和支持,我以“工学院民二七级(1938级)全体学生”的名义,草拟了一份“致全校教授先生书”(这份油印件是王前刻的蜡版,他一直保存着,解放后送给我了,十年浩劫中又得以幸存)。信中谈到当时北平、上海各大学校长、教授等对时局的表态和同情学生的言论,特别引用了陈衡哲的痛语:“横在我们眼前的路有四条:第一,是那浑浑噩噩的行尸走肉的路;第二,是那在‘刀头上舐血吃’的廉耻扫地的路。这两条是辱身亡国的死路;第三,是那‘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拼命的路;第四,是那忍辱食垢以求三年之艾的路。这两条是自救的活路。”信中接着说,“可是事实已明显摆在面前,吴越的故事已成史迹,别人早已做好了铁枷,使你再也不能做那‘生聚教训’的美梦。敌人侵占东北之后,而热河,而察哈尔,而平津,而整个华北。谁能担保不再而武汉……而全中国?这是最惨痛的凌迟。”当然,我们这时的认识是很幼稚的,根本不了解中国革命的主力是人民大众,竟这样夸大青年知识分子的作用:“现在唯有大学中的人们才是唤醒全国民众的泉源。‘五四’的力量永远光荣地留在历史上。”武大校长王星拱还算是一个尊重蔡元培办学精神的人(校长办公室挂着蔡的大幅照片)。教授和讲师中不乏爱国之士,也有进步的助教。哲学教育系教授范寿康讲辩证唯物论,最受进步同学欢迎。文学院长陈源(陈西滢)、法学院长杨端六、教务长皮宗石等则思想守旧。这封信当时是起了作用的,使许多教授包括王星拱同情学生的行动。
Copyright @2014-2022 www.hbdsw.org.cn All Rights Reserved
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版权所有,未经书面授权禁止使用
技术支持:荆楚网 鄂ICP备18025488号-1


微信公众号

手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