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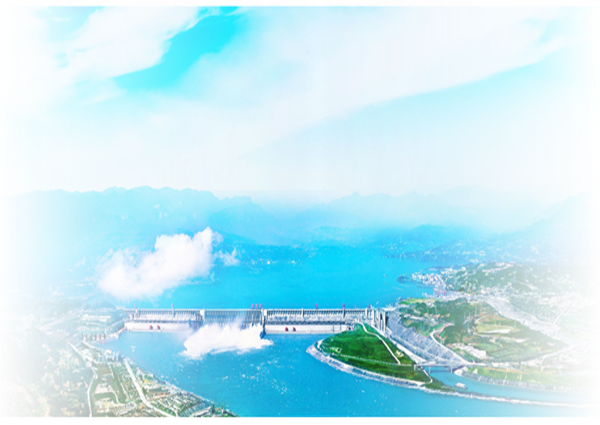
林 昶
1986—1987年间,在中葡关于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的谈判过程中,本人作为澳门的前线记者,参与了中葡谈判的采访和评论工作。相关的报导和评论文章,后来由澳门基金会以《中葡关系与澳门前途》的书名结集出版。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下称《澳门基本法》)起草和咨询工作期间,本人当选为澳门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的委员,直接参与了澳门基本法尤其是其中的“居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政治体制”章节的咨询工作,其间也撰写了不少评论文章。
在中葡谈判和起草《澳门基本法》过程中,本人感触最深的,莫过于中央政府认真倾听和尊重澳门居民的意见,并接纳了其中不少合理及可行的部分,使之化为《中葡联合声明》附件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澳门基本政策的具体说明》及《澳门基本法》的条文内容。这是完全符合中共“群众路线”的老传统及“澳人治澳”方针的。尤其是在中葡谈判开始时,内地刚结束十年“文化大革命”不久,部分澳门居民对内地情况及中央政府仍存在这样那样的误会,担心澳门回归后的政策未能完全反映澳门居民的意愿,甚至会有一些仍然带有“左”的残余痕迹,及在《澳门基本法》的起草和咨询工作进行的过程当中,又发生了“北京风波”,部分澳门居民对“北京风波”的认知有所偏差,因而担心中央政府在主导《澳门基本法》起草工作时,会掺入“北京风波”因素。因此,中央政府在中葡谈判中对澳门前途的安排,及中央政府对《澳门基本法》的立法主导原意和具体细节,能否听取澳门居民的不同意见,就使当时部分澳门居民充满了不确定感。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担忧是多余的。在中葡谈判及后来在起草《澳门基本法》的过程中,中央政府是认真倾听澳门居民的意见的。就以笔者而言,当时鲁平、诸华、莫瑞琼、周鼎、柯正平、胡厚诚、康冀民等中方官员,就曾分别与笔者谈话,询问笔者对相关问题的意见,并做了认真的记录。而本人只不过是一个“小人物”而已,当然是深受感动,并认为中央政府是如此重视本人这个“小人物”的意见,那么本人也就应当以认真、慎重的态度,实事求是、负责任地畅所欲言自己的一些看法,哪怕是当时被“主流社会”视为“邪端异说”、“跟红顶白”的观点。但意想不到的是,中央官员听完之后,还鼓励本人进一步独立思考,深入、全方位地研究分析澳门回归进程中各方面的问题,不要受“主流社会”流行观点的束缚。为此,本人大胆地提出了与当时“主流社会”相悖的一些论点,如针对前澳葡政府尙未向华人开放公共行政职位的情况,认为澳门缺乏治澳人才,如果不抓紧时间培训公共行政人才,并让他们在实践中得到锻炼,到澳门回归时可能就会出现“人才真空断层”。据说,正因为是中央在调査研究过程中,同样也捜集到与笔者相同或相近的类似意见,才及时提出“公务员本地化”、“法律本地化”及“中文官语化”的三大任务的过渡期工作目标,并向葡方施加压力,敦促葡方向华人青年开放公共行政职位,从而避免了在澳门回归时,当前澳葡政府中的葡人撤出后,华人尙未能接任的“不平稳衔接”的情况发生。对此,笔者是深有感触的,因为当时本人和黄汉强、杨允中等人提出类似的观点时,曾受到本地“主流社会”甚至是某中方驻澳官员(后来因犯贪污罪被判死刑)的呵斥,有人还给我们扣以“提出缺乏治澳人才就是企图以此为借口反对澳门回归”的政治大帽子。事实已经证明,还是我们的中央政府官员胸襟广阔,怀有包容及多元的精神,听得进并愿意接纳不同意见。
还有一件令本人深受感动的事,就是有关《中葡联合声明》签署仪式的中葡双方观礼人员名单安排及双方领导人演讲辞的翻译安排问题。在1987年3月26日《中葡联合声明》草签之后,笔者曾在澳门一家报社的《市民心声》专栏撰文指出,中葡双方在草签仪式上的安排欠妥:其一,在安排站到主宾席铁架上的人员时,中方凡是参与谈判工作的人员,包括外交部一些职位较为低级的工作人员,甚至是与中葡会谈关系不大的新闻司职员,都被安排站上了铁架。而在葡方方面,由前澳门政府派往北京参与会谈工作的罗庇度、苏宝明、林柏涛等三位翻译人员,却未被安排同一待遇。他们在北京期间,白天参与会谈工作,晚上又往往翻译会谈文件到深夜,甚至通宵达旦,为会谈的顺利进行作出了贡献,是十分有资格出席草签仪式并站上主宾席铁架的,但却被安排疏漏了。相反,在澳门电视台工作的葡国驻北京大使的女儿,却因放大假到北京探望父亲,被安排站上了铁架,既令人啼笑皆非,又令人颇不服气。其二,草签仪式当日,中方代表团团长周南和葡方代表团团长麦端纳的致词,竟同样都是由中方的翻译人员进行翻译,这是不符外交惯例的。如果说是葡方的几位翻译员(即罗庇度等三人)的普通话发音欠佳的话,那么,当天中方翻译员在将周南的致词译成葡语时,也非标准发音,而是带有巴西腔的葡语。如按对葡方翻译员的不信任态度,中方翻译员亦同样不应被安排担任草签仪式的现场翻译员。
过了几天,笔者又在《市民心声》专栏撰文,分析葡国社会民主党政府倒台一事与中葡关于澳门前途的联合声明不无关系。文中认为,葡国反对党——民主革新党为什么偏偏在席尔瓦总理(按:现任葡国总统)将到北京签署联合声明时提出对政府的不信任案?可能是故意令席尔瓦在赴北京正式签署联合声明时“难堪”,及为了对澳门问题的顺利解决挽回点政治“面子”;也可能是民主革新党因看不惯苏亚雷斯总统和社会民主党在澳门问题上出尽风头而放出的横枪暗箭。而席尔瓦以“看守政府总理”的身份签署联合声明,似乎欠缺了一些什么,尽管《中葡联合声明》的草案文本已经获得葡国国务委员会的许可。
还有一件中央政府乐于和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的事,就是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国际公约》《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简称两个“国际人权公约”,下同)纳入《澳门基本法》的问题。在《中葡联合声明》签署之时,葡萄牙虽然已于1978年就已加入了两个“国际人权公约”,但一直未将之延伸适用于澳门,故《中葡联合声明〉的附件一就未像《中英联合声明》的附件一那样,写上两个“国际人权公约”继续适用于澳门的规定将继续有效的内容。
在《澳门基本法》起草和咨询工作启动之后,本人在澳门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的会议中,提出了这个差异的问题,并建议《澳门基本法》应该弥补这个不足(当时已公布的《香港基本法》草案初稿,有相应的条文内容),以提高澳门居民的信心,及避免造成大香港小澳门的误会。但因当时是“北京风波”刚发生不久,有个别基本法草委会和咨委会的委员担心北京会将此建议与“民运诉求”挂钩,对本人不利,而劝说本人不要再纠缠这个问题。然而,一些中方官员与本人个别谈话之后,本人仍然坚持个人的观点,即认为既然香港有,澳门也应有,而且《澳门基本法》写上相关内容,更有利于增强澳门居民对未来的信心,消除对“北京风波”发生后的某些不稳定心理。他们一致同意我的观点,并鼓励本人不但可以继续提出类似问题,而且还要多设法为解决此类问题提出“解套”办法,尤其是如何在葡国尚未将两个“国际人权公约”延伸适用于澳门的情况下,争取将相关条文写进《澳门基本法》。
为此,本人提出了两点建议:一、中方通过外交途径,敦促葡方尽快而且必须抢在澳门基本法草委会向中国人大提出《澳门基本法(草案)》之前,宣布将两个“国际人权公约”延伸适用于澳门。二、倘葡方不配合,鉴于葡方已宣布将《欧洲人权公约》延伸适用于澳门,可考虑在《澳门基本法》上加入《欧洲人权公约》继续在澳门适用的内容。
兼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澳门基本法草委会副秘书长的原澳门新华社副社长胡厚诚和兼任草委会委员的前中葡联合联络小组中方组长康冀民大使,曾为此专门约见本人并指出,中国是亚洲国家,因而回归后直辖于中国中央政府的澳门特区,不宜继续适用《欧洲人权公约》,故而本人第二点建议,并不可行。不过,第一点建议则具有较高的合理性及可行性,故中葡联合联络小组中方小组已向葡方小组提出相关建议,有关葡国政府宣布将两个“国际人权公约”延伸适用于澳门的工作,正在进行之中。当然,为了防备万一相关工作赶不及在《澳门基本法》立法之前完成的情况,基本法草委会将会在草拟第三章《居民的权利和义务》时,认真参考两个“国际人权公约”的规定,尽可能地将《公约》中的有关内容吸收到《澳门基本法》中去。
幸而,在中方的积极敦促之下,终能赶在《澳门基本法》起草工作即将结束之际,在经过中葡两国政府的讨论、磋商后,葡国国会于1992年I2月7日以发布1992年第41号《国会决议》的方式,宣布将两个“国际人权公约”延伸适用于澳门,并在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举行的前一日,1993年1月12日,将此《国会决议》刊登在《澳门政府公报》,终使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能够专列一个条文——第四十条:“《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和《国际劳工公约》适用于澳门的有关规定继续有效,通过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法律予以实施。澳门居民享有的权利和自由,除依法规定外不得限制,此种限制不得与本条第一款规定抵触。”使《澳门基本法》终能赶在1993年3月31日在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
这几件发生在本人身上或与本人有关的事情,都充分显示出中央政府乐于及善于吸纳澳门居民包括“不同声音”在内的意见。在我看来,正是因为这种“走群众路线”的作风,才使得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及“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大业顺利成功。
(作者林昶,回归谈判时先后为《澳门论坛报》采访主任、《华澳邮报》主编,澳门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文章摘自《文史天地》2014年09期,有删减)
Copyright @2014-2022 www.hbdsw.org.cn All Rights Reserved
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版权所有,未经书面授权禁止使用
技术支持:荆楚网 鄂ICP备18025488号-1


微信公众号

手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