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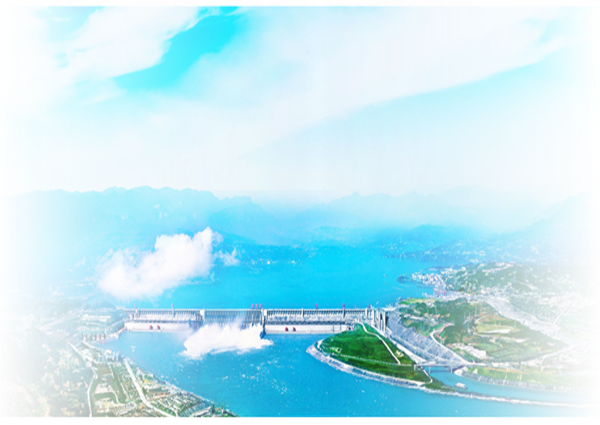
金冲及
五、我入党的特殊经历
要说我入党的经过,先得简单地讲一下当时复旦大学地下党组织的情况。
复旦大学创建于1905年,一直有着爱国主义和民主思想的传统。长期主持学校工作的是李登辉,他原是华侨,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复旦建校后四个多月就担任总教习,1913年任校长。他作风和治校开明,往往其他大学中因政治原因而被开除的学生,他都吸纳进复旦来(包括后来的校长章益在内),因此受到师生们的普遍尊敬。五四运动开始后十多天,5月15日,上海学生联合会成立,担任会长的便是复旦学生何葆仁。复旦大学的党组织成立于1925年。据1926年7月的统计,共有党员19人。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这年7月复旦仍有党员7人。以后,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下,在复旦,党所领导的爱国学生运动一直前赴后继地进行着。
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复旦因地处江湾,被日军占领。学校和党组织都分成两部分:重庆和上海。
一部分内迁大后方的师生员工几经辗转,经江西和贵州,抵达重庆北碚的夏坝,后改为国立大学。皖南事变后,在国民党当局严重白色恐怖下,党组织处境极为困难。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国民党统治区“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采取了多种巩固党、隐蔽党的措施,如缩小党的机构、建立互不知道的平行组织、停止发展党员等。
为了满足一些先进青年对组织起来的强烈要求,1943年秋,在中共南方局青委领导下建立一个名为“据点”的组织。它的成员不全是原来的共产党员。它既非党的组织,也非定型的群众组织;既没有名称,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又没有一定的章程、纲领和定期的会议制度。但是它遵守秘密工作原则,“据点”之间不发生横的来往;它的成员也知道自己的工作是有领导、有组织联系的活动,但国民党特务看不见、抓不着。“据点”这个名称是周恩来同志定的。这是在极端严酷的白色恐怖条件下,为着巧妙掩护党组织、隐蔽聚集革命力量和推进革命斗争所采用的极为特殊而有效的办法。
另一部分滞留上海的师生员工(包括李登辉校长在内),迁入上海租界内,几经搬迁,后到公共租界的赫德路(后改名常德路)上课。当时有学生410人、教员44人,其中党员12人,党支部由中共上海地下党学委领导。抗战期间,先后有共产党员49名。1944年7月,由中共中央华中局城工部任命张李为上海市学委书记、吴学谦等为委员,市学委所属国立大学区委书记是复旦大学社会系学生费瑛(解放后曾任青年团上海市委组织部长,“文革”前任上海戏剧学院党委书记)。
抗日战争胜利后,重庆部分师生员工在1946年8月才陆续抵达上海。由于情况复杂,两部分的党组织没有立刻合并,到1947年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时依然如此。但双方已相互了解,形成默契,在抗议美军暴行和反饥饿、反内战等运动中不分彼此、密切配合,形成实际上的统一体。这样,建立统一的党组织已具备条件。
上海部分的党组织在日本投降时有党员11名,1946年发展到39名,1947年夏季加上新入校的党员已有52名。他们中,土木工程系的党员最多。
1947年5月,中共南方局青年组决定在重庆迁往上海的党员中建立党支部,由史地系四年级学生金本富任支部书记,共有党员14人。他们中,新闻系的党员最多。
1947年9月,中共中央南方局所辖上海市委学委决定将上海和重庆两部分的党组织合并,建立中共复旦大学总支委员会。市学委副书记吴学谦代表学委宣布:大学区委书记费瑛为总支书记,金本富(不久因毕业离校,“文革”后曾任武汉市教育局长)为总支副书记,张渝民(原上海系统)、李汉煌(原重庆系统,解放后首任青年团上海市委秘书长,不久病故)为总支委员。
这正是我刚在复旦大学入学的时候。
我参加中国共产党有两次,但不是因为脱党或失去关系后重新入党,而是党的两个不同系统的组织几乎同时来发展我入党。
这两次入党都在1948年春夏之交,相隔大约一个月。第一次是四五月间,来发展我的是复旦史地系一年级的同班女同学卓家玮,她是属于南京市委上海联络站系统的。第二次是五六月间,来发展我的是我在复旦中学读书时关系最密切的同学、当时在复旦大学土木工程系一年级学习的邱慎初,他是属于上海市委系统的。
卓家玮那时刚从南京的中央大学实验中学毕业,在南京入党,1947年秋考入复旦大学史地系,她党的关系还在南京市委上海联络站。因为一起参加学校中接连不断的学生运动,她对我的政治观点和表现都很清楚。
她来发展我入党的方式很巧妙:因为在我还没有成为共产党员前,她不能先在一个非党员面前暴露自己的党员身份,所以在早一些时间就先跟我说:“我们是不是一起尽力去找共产党?如果你找到了,你就告诉我。如果我找到了,我就告诉你。”这样,她是以一个非党员的口气对我说的,并没有暴露她的党员身份。我当然表示十分赞成。
过了一些时间,她忽然对我说:“有人要我们两人入党,你看我们要不要参加?”这个办法确实很好:如果我表现得有些犹豫,她可以立刻说:我们还是不要去参加吧。这样,她还是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如果我的反应十分积极,那就可以进一步谈了。我当然没有一丝犹豫,立刻表示赞同。她就说他们要我们各写一份自传,把自己过去的经历、社会关系、思想变化的过程、对共产党的认识、为什么要入党等写清楚。当我写自传的时候,她装作也在写自传。
我这份自传写得十分详细,对自己经历中遇到过的事情都写得很清楚。
自传交去后,她告诉我,组织已经批准了。星期日,会有人到你家来,说是她介绍的,那就是来接关系的。到了那天,果然有一个戴眼镜的男同志来我家。他大约比我大六七岁,在那时看起来比我年长得多,说是姓何,是卓家玮要他找我的。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看来不是复旦的同学。我也不好问他的名字和情况。他先问问我的情况,然后说,以后他会定期到我家来的,现阶段主要是帮助我学习。
我当时兴奋的是可以入党了,至于这一天究竟是几月几日,我当时没有查。而在当时严酷的白色恐怖下,地下党对这类事绝不会有任何文字记录留存下来,那是纪律所不容许的,只能在解放后凭当事人的记忆来说,有时还需要有当事人证明。我在几十年后曾对贺崇寅(即“老何”)说过大概是1948年5月。以后,当时地下党联系卓家玮的程极明(新闻系一年级同学,解放前夕担任复旦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解放后曾任国际学联书记处书记、世界经济研究会副会长)说是4月。总之,说1948年四五月间一个星期天,那是不会错的。
说来也巧。就在同“老何”接上关系后没有多久,邱慎初来找我。他是1948年3月由何志禹介绍入党的,入党还不久,对党的规矩还不太懂,我们的关系又太密切,所以没有绕什么圈子,就直截了当地对我说:党组织已经决定发展你入党了,你赶快写自传。我对党的规矩也没有怎么懂,同他又太熟,相互间完全信任,就告诉他我已经入党了。他大吃一惊,问我是谁介绍的,我说是卓家玮。隔几天,邱慎初很紧张地告诉我:组织上说,党内没有这个人。再多的情况,他也说不出来。我一下就慌了,急忙问他:那怎么办呢?他说不要紧,你再写一份自传给我。这样,我就写了第二份自传。
6月5日,邱慎初告诉我:组织上已经批准你入党了,会有人来同你接关系,暗号是送你一本书。翻开来,书上第一页盖有邱慎初的图章,那就是。
为什么这天的月日我都记得?并不是当时就记住了,只是因为我清楚地记得是“反美扶日”大游行那天的早晨。那次大游行的日期上海各报上都登载了,所以一查就查到了。
到邱慎初所讲的那一天,有人按照暗号到宿舍里找到我。这次来的人我认识,是新闻系二年级的同学江浓(台湾人,他以后说过自己是台湾的第一批中国共产党党员,到复旦来读书,是为了便于熟悉大陆的情况),我前几天刚见过。谈的中间,我问他原来我加入的那个组织是怎么回事。他说:“大约是托派(那时候,对自称是共产党员而查下来党组织内又没有这个人,往往就认为是托派),不过不要紧,组织上对你是了解的。”我很着急,问他这事以后怎么办?他说:“你继续保持同他们的关系,注意进一步观察。”
这些情况,“老何”根本不知道。他仍过一段时间就约好到我家里来,主要是给我分析当时的政治形势,帮助我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并没有安排我在复旦的行动任务。这种关系保持了三个月,我“观察”来“观察”去,始终没有发现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有一次,我憋不住了,在学习中直截了当地问他:托派是怎么回事?他分析了一番。我觉得他讲的也很正确。这下,我就更糊涂了。
八九月间,国民党特种刑事法庭在各地对进步学生进行大逮捕,我受到传讯和通缉,根据党组织要求藏匿起来。江浓找我谈话时,我问他:那个组织怎么办?他说:“甩了吧。”我就没有同“老何”联系。
上海一解放,我回到学校。遇到正担任上海学联组织部长的程极明,我们也是极熟的朋友。他是1946年在南京入党的,组织关系到1949年初才从南京市委系统转到上海市委系统。他问我:大逮捕后你到哪里去了?组织上本来准备送你到解放区去,可是找不到你了。我就把前面所说的那些情况详细地同他讲了一遍。他告诉我那个组织是南京市委上海联络站,同上海市委的党组织不发生横的联系。“老何”的名字叫贺崇寅,是联络站负责人,直接受地下党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领导,现在是上海总工会秘书处处长,并且陪我去看望了一次贺崇寅。不久,他又告诉我:卓家玮在建国后不久就因病去世了。
类似的情况,当时我还听说过不少。组织上曾告诉我:化学系有个同学郑某(名字忘了,只记得是个单名)是“托派”。但解放初我曾在上海市委见过他。更离奇的是:江浓告诉我,和他同在新闻系二年级的两个同学杨本驹和吴友被一个自称共产党员的政治系同学吴怀书送到解放区去了,但吴怀书并不是党员。他讲了后很伤感地说:“他们两个现在可能都关在国民党的集中营里了。”实际上,杨本驹顺利地到解放区后长期在新华社工作,改名为袁木(后曾任国务院研究室主任)。以后,我同他一起起草文件时,曾问他:“你到解放区去,是不是吴怀书介绍的?”他说:“是的。”可见原来对吴怀书的怀疑也是完全错误的,同时可见地下党当时所处环境多么复杂。
把话再说回来:为什么南京市委要在上海设立这样一个联络站?
上世纪90年代,贺崇寅到北京来,给我打电话要我去看他,说他住的地方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由喜贵安排的,他这次来北京是来看望江泽民同志的。去后,我就问他上面提到的那个问题。他说:那是地下党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同志在1947年4月布置给他的任务。解放后,他写过一份材料讲到陈修良布置这项工作时所讲的话,并说记下的这段话经陈修良看过。
陈修良同志当时说:“南京有不少党员因各种关系不得不撤退到上海,其中有的是为了政治避难,有的是已经考取了大学或就业,等等。这些党员本来都可以转给上海党组织的,但由于政治环境十分险恶,由南京转来的党员中有的面目已经暴露,留在南京很危险,转到上海,也恐牵连上海党组织。因此经中共中央上海分局决定,暂时不把这些南京党员的组织关系转到上海,单独建立一个联络站,仍由南京市委领导。这个联络站的任务是保存实力,而不是开展群众工作,这一点你要特别注意。组织生活的内容主要是学习形势和理论。”后来她又补充说明:这些党员“只能以一个积极分子的面目出现参加一些群众性的活动,不可暴露身份,随便发生横的关系。”
这样,我才明白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也才了解为什么“老何”每次来都只是帮助我学习形势和理论,从来不谈具体工作。有一次我向江泽民同志谈起贺崇寅,说我本来只知道他叫“老何”,江泽民同志说:我那时只知道他叫老徐。
复旦的地下党组织系统还有不少,都没有发生横的关系。单以我所知道的再举几个例子:
苏南军区在复旦也有个组织。农学院的女同学夏佩荣(解放后在农业部工作)后来告诉我:她就是这个系统的地下党员,曾要发展上海市委系统在农学院同学中的党员袁识先“入党”。上海的党组织也要袁识先参加进去“观察”,参加后就由夏佩荣联系。上海解放前夜,苏南军区地下党这部分组织同上海市委系统的组织合并,袁识先入党比夏佩荣早,年龄也大,就由他联系夏佩荣。夏佩荣解放后告诉我:“本来是我领导袁识先的,一下就变成袁识先领导我了。”
苏南还有个茅山工委也到复旦发展组织。1948年10月决定成立上海总支,由我也认识的新闻系同学罗我白任总支书记。在复旦大学也建立支部,由曾朝棣任复旦支部书记,在复旦发展党员。我熟悉的新闻系同学陈方树、练福和就是由他们发展入党的。上海解放后,这部分党员大体上都到苏南地区去工作了。
史地系二年级同学陈金灿后来告诉我:他是福建根据地的组织发展入党的。解放后去福建工作。改革开放后,曾担任中共福建省委办公厅主任(也可能是副主任)。
据说,上海局外县工委、浙东临委、苏中和淮南根据地党组织也曾在复旦发展党员,互不打通关系。对他们的情况,我完全不清楚了。情况如此复杂,彼此间绝不打通横的关系,有时甚至会发生误会,如程极明组织召开一些会时,上海系统的党组织还特地派人进去观察他们所谈的内容,准备应对。
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特殊而又复杂的做法?因为国民党当局特务机关实行白色恐怖的手段既凶狠又狡猾,以往有过不少血的教训:一处党组织被破坏,往往牵连一片,牺牲许多优秀的同志。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特务破坏各地党组织活动的手段更加周密和毒辣。中共中央在1941年5月接连发出《关于大后方党组织工作的指示》和《关于隐蔽和撤退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力量的指示》。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连续开会,要求各级党从组织形式到工作方法实行完全的转变:各地方党组织同公开机关脱离联系,缩小各级领导机构,建立平行支部,实行单线联系,各组织之间不发生横的关系,严格秘密工作制度等。这年7月,中共江西省委遭国民党特务机关破坏,省委书记被捕。8月23日,周恩来致电由南方局领导的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书记方方:坚决建立自下而上的平行组织;党员转地方不接关系,仍由原地原人联系。
中共党组织在国民党区域遭受的一次最大破坏是发生在1942年的“南委事件”。这年5月,南委派遣到江西检查工作的组织部长郭潜不遵守严格规定而被捕,并很快叛变,带领特务逮捕正在南委驻地曲江的廖承志和南委副书记张文彬、粤北省委书记李大林、广西省工委副书记苏蔓等。南方局立刻决定:南委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一律暂时停止活动,防止事件继续扩大。不久又决定南委领导取消,原有工作在南方局直接领导下重新得到发展,并采取了更严格的防护措施。
由于周恩来先后主持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南京局规定并坚持灵活多样的活动方式和极端严格的纪律,整个解放战争期间,上海的学生运动蓬勃开展而党组织从来没有遭受过一次破坏,这样巨大的成功来自以鲜血代价换来的沉痛教训。
再讲讲我第一次党的组织生活和入党不久后的反美扶日运动。
我经历的南京市委联络站活动,只是贺崇寅对我的单线联系,没有第三人在场。而上海市委系统发展我入党后,江浓就通知我到复旦以北不远的叶家花园(正式名称是澄衷疗养院)开党小组会。到的一共四个人。那里人很少,坐在草地上就像聊天那样,并不引人注意。四个人中,除江浓和我外,都是史地系我极熟的人:吕明伦、陶承先。陶承先(后改名陶牧,解放后长期在广东办报)是史地学会会长,平时我们常在一起,这次和我同时入党,可以说意料之中。吕明伦却使我吃惊,因为他就和我住在一间学生宿舍内,四个人朝夕相处。他年岁比我们大,在我眼中已显苍老。对他的政治态度,我当然了解,但他平时讲话很少,从没听到他长篇大论地发过议论,不料他早是共产党员了。
会上主要是江浓讲话,除讲形势和党内纪律外,主要是正在展开的“反美扶日”运动。
“反美扶日”是一个简称,比较完整地说就是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复活。那时离抗日战争胜利才两年多,创痛犹存,这个问题一提出,人们旧仇新恨一齐涌上心头,有极广泛的群众基础。运动一步一步展开,有条不紊,计划周密,得到广泛社会阶层的支持。国民党当局一时也不便立刻公开阻挠。
史地系在这次运动中走在前头。3月31日,史地学会举办晚会,请日本问题专家李纯青来作题为《复兴中的日本》的讲演,列举事实,揭发美国正在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接着又请孟宪章教授来作《日本问题》的讲演。
合作系同学出了十多版的大幅剪报,分门别类地用报刊资料揭发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的具体事实,还有漫画,很有刺激力,在学校里引起很大轰动。
4月1日,“缪斯社”等三团体在登辉堂演出《黄河大合唱》。由新闻系同学司徒汉指挥。他的指挥充满激情,整个大合唱产生巨大的感染力。在学校里演出后,又开着卡车先后到交通大学和圣约翰大学演出,也引起强烈反响。这两次外出演出,我都随着去了。
那时也有一些说法:你们是学生,首先应该好好读书,不要去搞那么多活动。周谷城教授讲了一句话,我至今难忘。他说:“你们第一是中国人,第二才是学生。”这话很能打动同学们的心。
5月4日,全市1.5万名学生在交大民主广场举行篝火晚会,也请孟宪章教授做“反美扶日”的主题报告,会上宣布成立“上海市学生反对美国扶植日本、抢救民族危机联合会”。我也去参加了。5月30日起,复旦的反美扶日运动走向高潮。5月30日是个星期日,这天400多名复旦同学组成30多个小队,到南市和上海美专、立信会计学校等进行宣传和演出,收到良好效果。
当晚,在校内举行五卅晚会,主题自然是反美扶日。本来安排在子彬院101大教室开。由于去的人太多,坐不下,临时涌到登辉堂举行(平时不经校方批准,学生是决不能到那里开会的)。这次参加会议的教授很多,有张志让、陈望道、周谷城、潘震亚、章靳以、方令孺、张孟闻等。张志让教授第一个发言,还有好几个教授讲了话。这在以前不曾有过。
第二天开始,校内举行“反美扶日周”,围绕这个中心,每天有一个主题,如:“回忆日”“通讯日”“歌咏日”“展览日”。这大概是模仿抗战初武汉时期政治部第三厅的做法,显得很有声势和吸引力。
6月5日,全市学生准备在外滩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复旦同学准备集合赶往外滩参加示威。集合人数有1800多人,先在校内绕大草坪周围游行,唱着歌,喊着口号,队伍的首尾刚好衔接。这样的规模过去在复旦从来没有过。大家都很兴奋。
对这次活动,国民党当局下狠心作了充分准备来阻挠。队伍正要出发,校门已经关闭并且上了锁。同学们转向校门东侧的篮球场边门出去,门外密聚的军警已支起汤姆逊式冲锋枪,还有装甲车堵住大路。队伍只得掉头从校园北面的后门出去,绕道田野小路前进,将到大八寺时,国民党军警的马队已先赶到,堵住了前进的道路,嚷道:“今天不能进市区。”谈判也没有结果。双方相持很久。同学们越来越愤怒,一部分同学已积压了很长时间的愤怒,大声叫道:“冲过去!”游行主席团(实际上由地下党主持)比较冷静,看清冲过去必将造成流血惨剧,并且得到消息,交通大学的队伍在1000多名武装军警严密包围下已改为校内示威游行,市区内各要道密布军警,大多数学校的队伍也没有能到达外滩集合,便果断决定将队伍全部带回学校。我一直在队伍里,有过以往的经验教训,明白这个决断是完全正确的。
但队伍也不能回到学校就解散了,那样对士气是不利的。所以回到校内后,大部分同学在新闻馆前小广场上集合,由游行主席团讲话,还由新闻系一年级同学演出活报剧,一个高个子(梁增寿)演美国人,一个矮而戴眼镜的(武振平)演日本军官,表演他们之间的相互勾结。活动结束后,队伍才解散。同学们在这次行动中受到深刻教育,又避免了重大损失。周谷城教授也对同学说:“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是长期的斗争,不能认为游行没有成功,就是运动失败。”
这时已近暑假。校方匆匆忙忙地结束本学期的课程,提前宣布放假。相当多同学回家。留校的人大大减少。我家在上海,也回去了。
Copyright @2014-2022 www.hbdsw.org.cn All Rights Reserved
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版权所有,未经书面授权禁止使用
技术支持:荆楚网 鄂ICP备18025488号-1


微信公众号

手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