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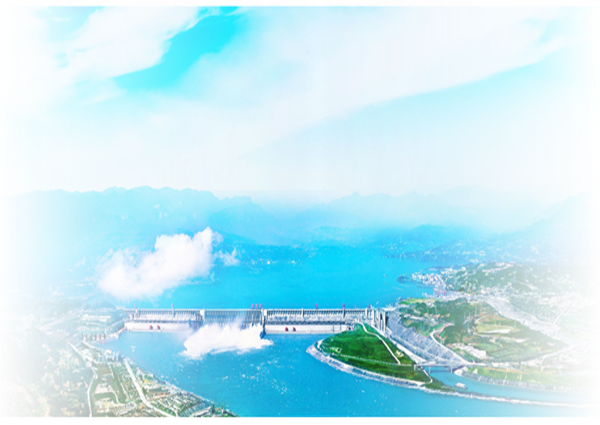
胡铭心
1949年5月16日,汉口解放。但一江之隔的武昌却成了政权的“真空”地带。武昌市面谣言四起,一日数惊,人心惶惶。
24岁的我当时是中共地下党武昌中学联合支部的书记,负责湖北省女一中、实验中学、国立临时中学、省立临时中学、启黄中学、荆南中学、童军师范、大江中学等14个中学的“护产、护校、迎接解放”工作。这天下午,正当我忙得不可开交时,我的领导人杨坤泉跑来说:“把工作交给刘佩云,跟我走吧,有新任务。”
杨坤泉是清华大学的学生,也是24岁。1948年六七月间,他受党的派遣,从北京调来武汉,负责武汉的青年工作。我跟着杨坤泉来到了司门口一家印刷店,上了楼,只见吕乃强坐在一大堆稿纸前面,正写着什么。吕乃强也是清华大学学生,是1949年1月来武汉的。他看见我们两个上来,把稿子一推,握住我的手,笑着说:“欢迎,欢迎,这下子我们《新武汉报》编辑部成员齐了。”杨坤泉看我莫名其妙,笑道:“地下党决定编一份党的报纸,来迎接解放,明天就出刊,调你来工作。”
我茫然道:“就我们三个人?”杨坤泉说,“暂时就我们三个。”我道,“我可从来没有办过报刊。”吕乃强说,“我们也没有办过,我只在大学办过墙报。管他呢,明天先出一期八开的快报再说。我和老杨算编辑,你算外勤记者。时间不多了,这就干起来。”说罢,从口袋里掏出个袖章来,说道,“套上它,这就出去采访吧!”我接过袖章一看,它是白色的,5寸宽,上面印着一排红字,“武汉商民自卫大队”。吕乃强道:“现在天已经黑了,套上它安全些,今晚的口令是‘保卫安全’。”
我套上袖章,走出门来,执行毕生头一次的采访任务。
这天晚上8点钟左右,我来到了武昌最热闹的地方司门口。但街面上是冷清清的,没一个行人,也见不着警察,店铺都关着门。这个时候去采访谁?突然,我听到远处有零落的枪声,我灵机一动,就决定去采访商民自卫大队。
商民自卫大队的大队部设在阅马场红楼里。我沿着胡林翼路(今民主路)往上走,准备穿过蛇山洞,迎头掷来一声大吼:“口令!”我立刻站住脚,也大声回道:“保卫安全!”这时候可误会不得。于是,立刻从黑暗中走过来5个人,也带着白臂章,手里一律提着长棍,穿的却是平民服式,这显然就是商民自卫队的队员们了。他们用手电筒晃了我一下,大概看清了我的臂章,立刻变得友好起来,其中一个人道:“这么晚了,一个人在街上走,也不怕有人打你的冷枪、闷棍?”我笑道,“谁这么大胆敢谋财害命?”那人道,“难说得很,什么溃兵游勇、地痞流氓、‘吃光队’,都冒出来了,你还是小心些好!”
我谢了他们的好意,便穿过蛇山洞,来到了红楼。一进去,便被紧张气氛震住了:只见到处是人,有的成队进进出出,有的背着枪攀在发动了的4辆消防车上,有的聚在一起大声议论什么,电话铃也不停地在响……大厅上一群人围在3张拼拢的办公桌旁,有人大声地在发号施令。
我从人堆里找到一个看上去像“领袖”的人问道:“汉口方面有消息没有?”
“没有,不通轮渡,又不通电话,什么消息也没有,真急死人,看来解放军天亮才会过来了!”
我又问道:“鲁道源的部队退到了哪里?会不会反扑回来?”
他哈哈笑起来,说道:“这群兔崽子跑得好快,已经跑过羊楼司(今赤壁市下辖一小镇)了!反扑回来?借给他一万个胆子谅他也不敢。”
“‘吃光队’有动静么?”
他道:“一个小时前在凤凰山方向和我们打了一仗,纱厂的纠察队和我们配合,大获全胜,看来成股的‘吃光队’已经不成气候了———不过也难说,我们警惕着呢!你不见院子里突击队都坐在消防车上整装待发么?”
“警察局呢?怎么大街上没见一个警察?”
“他们?”他撇了撇嘴说:“平素欺侮老百姓算他能!碰到节骨眼上,早躲起来了。他们怕新政府找他们算旧账呢!”
“那末,你们自卫队一共有多少人呢?”
“3000。”他自豪地说道,“一有事,各工厂、学校的纠察队随传随到!你放心,我们老百姓有力量,保得一方安全。”
我从红楼出来,心头一畅,尽管街道上依旧杳无一人,风凉飕飕的,可是我安心了。因为我知道有几千人已武装起来,他们彻夜守卫着武昌。
我赶回编辑部一说,吕乃强道:“好!写出来,1000字,即刻要!”我拖过一张板凳,席地坐下,不到半个小时即刻交了稿。杨坤泉看了看,说:“行!你再出去采访一下如何?”我又是二话没说,起来就走。吕乃强道:“喝杯热茶,歇口气嘛!”我道:“不用了,我不渴。”杨坤泉追着我的背影喊道:“你小心点。”
这次去哪里采访呢?我忽然想到不妨到学校去看看,实验中学离司门口不远,再说,我也牵挂着“新青联”的同志们,不知他们的工作搞得怎么样了?
待我走到中华路口时,已是子夜。忽听得卖水饺的摊子上传来“笃笃”的敲竹梆声,我这才想起晚饭还没有吃呢,肚子饿了。我买了两碗水饺,在长板凳上坐下来吃。那卖水饺的大概有60多岁了,我问道:“这么晚了还做生意?兵荒马乱的,你不怕?”那老汉道,“不做吃什么?我们穷人又有什么怕的?有钱人才怕共产党呢!”我笑道,“你真的不怕?”他摇头道,“真不怕!‘刮民党’整得我好苦,他们不败,叫做没得天理,变了天,总会好些。”我―下子感到和他亲近起来,问道:“今晚生意怎么样?”他笑道,“今晚生意特别好。”刚说到这里,我身后一扇门“呀”的一声开了,一个女人出来,买了6碗水饺。等他好一阵忙完,才接着对我说:“没人睡觉呢,你别看家家户户关着门,门里都点着灯呢!”我道,“他们是怕得睡不着觉?”老汉道,“除了有钱人,有谁害怕?有钱人、当官的只怕早就跑光了。我看多半人是喜得睡不着呢!”这时,陆陆续续又有人来买水饺。
吃过水饺,我便向实验中学校门走去。实验中学校门铁栅子紧禁闭,门里10多个男生拿着童子军棍守着,他们警惕性很高,怎么说也不放我进去。我说:“那么,你们叫田文生出来说几句话总可以吧。”田文生是实验中学“新青联”组长,我同他是1948年底认识的。他听到传唤,一会儿就出来了,见是我,喜道:“是胡老师来了,快进来,快进来。”
我道:“你们的纠察队怪不错的。”他道,“里面有几个‘新青联’成员领着,纪律还严明,我们和商专、省二女中联防,互通消息的。”我道,“学生都到学校来了?”他说,“绝大多数来了,护校嘛,谁不关心?”
此时,校内各个教室里灯火通明,笑语喧天,《解放区的天》《团结就是力量》等歌曲响彻校园。我说:“好啊!都学会唱进步歌曲了?”他自豪地道,“都会唱了,会唱十几支歌呢!全是我们组织歌咏队教的,平时只低声哼,今晚上可就放开喉咙唱了!”我们沿着一排排教室走过去,只见他们都在忙着做纸旗,写标语,贴横幅,扭秧歌。田文生告诉我:“这是在准备明天上街迎接解放军呢!”我道,“一夜不睡,他们不饿么?”田文生道,“大厨房蒸有馒头呢!你饿不饿?多得很呢!”我笑道:“谢谢,我在门口吃了两碗水饺。不过,你最好把同学组织一下,轮班睡觉,别熬得太狠了,小青年瞌睡大。”田文生摊开手,摇头道:“我们原也组织了的,分上、下夜两班,可没一个人肯去睡,这样的夜晚一生也难得碰上一次,这是迎接黎明,迎接日出呢!”我笑道,“不错,这才是‘阴阳割昏晓’呢!要是能照张像可就好了!”田文生道,“是啊!可是全校师生一部照相机也没有。”田文生伸过手来,和我紧紧地握着,两眼放着熠熠的光。
田文生送我出来,在校门口碰见几个女生挟着标语,提着浆糊桶。我问道:“这就出去贴标语?”田文生道,“早些贴,天亮了,老百姓一出门,就能看到,效果好些。”我点点头,“也是,只是必须派人护送,大意不得,此刻还不算是我们的天下呢!”田文生说,“对。”立刻招来一小队纠察,跟着她们去了。
我缓缓地跟在她们后面,她们贴一张,我看一张:“热烈欢迎解放军同志!”“天亮了!”“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打倒蒋介石!”
回到编辑部,只见楼下的排字工人正紧张地捡字、拼版,忙得头也抬不起来。上了楼,满房烟雾腾腾,吕乃强和杨坤泉还在写着什么。我坐下来就赶写我的第二篇采访稿。待等写完,天已经亮了。忽听得不知何处燃起了爆竹,起初是稀稀落落的,但一会儿竟响成一片,彷佛全城都在鸣放鞭炮。我们三个人打开窗户向下望去,喝!满街是人,都在大声说话,满脸堆着笑。吕乃强道:“我们也下去走走吧!”
我们走上街去。远远传来锣鼓声,看哪:华中大学的队伍来了,一队人舞着霸王鞭开路;中华大学的队伍来了,他们几百人扭着秧歌;纱厂工人的队伍来了,女的穿白围裙,男的穿工作服;沙洋中学、省立临时中学、省实验中学、省二女中、商专、童军师范队伍也来了,他们整齐地挥舞着三角形彩棒,唱着各种革命歌曲;商民自卫队的队伍也来了,除了棍棒外,竟然还背着百来支步枪。艺专、安徽中学、省一女中、省一男中从正街上过来会合,他们的队伍里还有人化了装,扮演解放军押着垮了台的蒋介石。
街上人山人海,一片欢腾。我满眶热泪,嘴里只是叨念:“解放了,终于解放了,我等到这一天了!”不觉地把背脊挺了起来,只觉得人人都可爱,人人都是亲人。
9点钟,汉口过来几条轮船,渡过来第一批解放军战士。武昌新生了。武汉新生了。
(作者时系中共地下党武昌中学联合支部书记,曾任湖北大学图书馆馆长。来源:《武汉文史资料》2009年Z1期)
Copyright @2014-2022 www.hbdsw.org.cn All Rights Reserved
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版权所有,未经书面授权禁止使用
技术支持:荆楚网 鄂ICP备18025488号-1


微信公众号

手机版